危地马拉确认此前发现玛雅城市遗址年代
危地马拉确认此前发现玛雅城市遗址年代
危地马拉确认此前发现玛雅城市遗址年代新华社北京5月(yuè)30日电 5月30日,《新华每日电讯》发表题为《走进(zǒujìn)中国科学家博物馆感悟“科学家精神”》的报道。
“推开博物馆厚重的玻璃门,仿佛踏入一道(yīdào)时空裂隙。这里没有网红展(wǎnghóngzhǎn)的浮躁(fúzào)喧嚣,只有泛黄手稿上的墨迹沉默翻涌,沙盘剧场的风声低吟着戈壁往事,以及一群把名字刻进星河的人,用(yòng)一生写下的答案。”
网友“媛媛不圆”在社交媒体上的(de)这段笔记,击中了(le)记者心中最柔软的部分。我们都在一个春日(chūnrì)邂逅了一座让人激情澎湃的博物馆,在里面找到了共和国的“国家宝藏”。
这座博物馆(bówùguǎn)就是中国科学家博物馆。它位于北京城中轴线北端的奥林匹克中心区,与中国科学技术馆一街之隔、廊桥相连(xiānglián),是全世界首个以国家名义为科学家群体建立、弘扬科学家精神、打造(dǎzào)科技(kējì)工作者精神殿堂的博物馆。
走进(zǒujìn)7500平方米(píngfāngmǐ)的展厅,宛如踏入浩瀚无垠的时空长廊:李四光、竺可桢、钱学森、王淦昌(wánggànchāng)……这些熟悉的名字,如雷贯耳,他们的功业,国人早已耳熟能详。而更多的,是一个个有些陌生的名字,但无一例外,他们每个人,都(dōu)是一片星空中最为闪亮的那一颗。
 和中国科技馆一路之隔的中国科学家博物馆(bówùguǎn)。新华每日电讯记者李牧鸣摄(shè)修史立典
“你知道吗?1999年我国隆重表彰的‘两弹一星’元勋有23位,可当年参与‘两弹一星’工程的科技工作者总共(zǒnggòng)有多少人(rén)?”中国科学家博物馆副馆长孟令耘(mènglìngyún)一下子问住了记者。
“据我们了解,光中国科学院系统参与的就超过1.7万人(wànrén)!但即使这(zhè)23位功勋科学家,大家(dàjiā)熟知的可能也不超过五六人。”孟令耘说。
的(de)确,因为资料保存不够、挖掘宣传不多,很多参与“两弹一星”工程的科技工作者没有留下只言片语甚至姓名(xìngmíng),能(néng)让后来者了解他们所作出的重要(zhòngyào)贡献。这,就是启动挖掘共和国“国家宝藏”工程的初衷。
在中国科学家博物馆三层(sāncéng)最(zuì)不起眼的一隅,“藏”着撑起(chēngqǐ)这座博物馆的庞大工程——“老科学家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程”(以下简称采集工程)。
这个(zhègè)(gè)看不见“热火朝天施工场面”的(de)大国工程,2009年经(niánjīng)国务院批准,由中国科协联合中组部等11个部委共同组织实施。15年来,已先后(xiānhòu)启动700多位(duōwèi)科学家(kēxuéjiā)的资料采集工作,获得实物原件15.9万件、数字化资料45.6万件、视频资料50.3万分钟、音频资料59.6万分钟,涵盖了中国科学家的书信、手稿、科学仪器、著作、音视频和记录中国科技发展重大事件的相关文物、文献等珍贵史料。
“这个‘工程’的(de)启动既是酝酿已久,也是机缘巧合(jīyuánqiǎohé)。”从立项到跟进,直至现在都一直参与其中的孟令耘回忆。
2009年5月,中国科协对(duì)两院院士(yuànshì)年龄情况进行了一次摸底调查。结果显示,当时中科院院士在世687人,平均年龄74.8岁(suì);工程院院士在世712人,平均年龄73.5岁;每年去世的院士在20人左右,平均每个(měigè)月就有两位院士离世。
老科学家是共和国建设的(de)重要参与者,是中国现当代科技发展的亲历者和见证者,他们的学术成长历程本身就是科技史(kējìshǐ)的重要组成部分。每位老科学家的离世都是其所在领域(lǐngyù)的重大损失,而相关(xiāngguān)资料的散失也是科技史研究的缺憾。
时任中国科协调研宣传部部长的王春法(wángchūnfǎ)提出一个想法:老一辈科学家很多已是90多岁高龄,如果再不(bù)及时抢救发掘他们的珍贵资料,后人研究共和国科技史时,比如某个决策是如何做出的,哪些人在(zài)关键节点发挥了什么作用,很多细节就湮没在历史(lìshǐ)的长河里了。
说干就干,王春法组织起草了一篇题为《老科学家学术(xuéshù)成长历史资料亟待抢救》的专题调研报告上报国务院(guówùyuàn),很快获批实施。采集工程2009年(nián)当年即拉开序幕。
如今(rújīn),这份(zhèfèn)触发共和国科技史修史工程的三千字报告,首页复印件就静静躺在博物馆三层的展板上,仿佛是带着我们穿越(chuānyuè)“时空裂隙”的“月光宝盒”。
可是资料由谁采集?怎么采集?如何保存?没有先例可循(kěxún)。
这是一项庞大复杂的(de)系统工程。孟令耘介绍,团队组织了科技史、图书馆、科技政策等方面(fāngmiàn)的专家,用(yòng)5个月的时间讨论(tǎolùn)研究出17项采集工程的标准、流程、规范等制度文件,包括怎么组建采集小组,怎么培训,采集到的资料怎么归档、编目,音视频使用什么(shénme)标准、格式,整理出来的资料怎么保存、利用,以及知识产权等问题。文件经2017年再次修订,现已成为国内(guónèi)人物,特别(tèbié)是科技人物信息采集业内公认的标准和流程。
按照这个标准和流程(liúchéng),每个采集小组对应(duìyìng)一位老科学家,小组人员(rényuán)搭配(dāpèi)科学合理:要有老科学家身边比较(bǐjiào)亲近的人,比如亲属、秘书或者学生,方便沟通和获取资料;必须有科技史方面的专家,对资料的科学性进行审定;还要有档案专家,对资料进行编目和规范整理;以及音视频拍摄人员等。
采集的最后成果,要形成一份15万字左右的学术性研究报告。而现已正式出版的180多部传记(zhuànjì)丛书,均成为记录(jìlù)共和国各个学科、各门工程技术发展历程的基础(jīchǔ)文献。
在博物馆(bówùguǎn)“采集工程”展厅,一整面墙的书架上,已出版的科学家传记静待读者(dúzhě)。与之遥相呼应,这套丛书也正摆在中科院图书馆“科技自立自强”专题文献(wénxiàn)展的醒目位置。
“这一丰富而庞大的学术成长(chéngzhǎng)资料库,有助于研究者(yánjiūzhě)厘清中国(zhōngguó)科技界的学术传承脉络,是(shì)共和国科技史的宝贵财富。”北京大学科学技术(kēxuéjìshù)与医学史系主任张藜是采集(cǎijí)工程首席科学家,“陪伴”采集工程15年的她,一度放下自己的学术研究,一个个地打电话,一家家地上门拜访,一次次地向老科学家和家属们保证:国家一定会好好保管捐赠的实物原件,一定会建一个平台永久珍藏。
“就是这样琐碎(suǒsuì)地收集、细致地整理、精心地挖掘,目前共发动全国500多家单位参与,超过(chāoguò)5000名采集人员投身(tóushēn)其中,接续15年的努力,才有今天的成果。”孟令耘说。
孟令耘向记者讲述了已于(yǐyú)2020年去世的专家组成员樊洪业先生的故事。他是中国近现代科学史方面的大家,曾花费十几年时间整理编撰了24卷《竺可桢全集(quánjí)》。樊洪业陪伴采集(cǎijí)工程(gōngchéng)整整十年,在每一次采集小组的评审会上,总是提出(tíchū)尖锐但极其中肯的修改意见。他是“采集工程最年长的志愿者”。
“在生命的最后几年,他(tā)几近失明,还是坚持把装有手稿资料的笔记本电脑拿到跟前,调大字号逐字逐句审看,让我们非常感动。正因为有一批把这项(zhèxiàng)工作(gōngzuò)作为毕生事业追求的专家,才使采集工程15年来保持一贯的高(gāo)学术水准。”孟令耘说。
采集工程也是一个“双向奔赴(bēnfù)”的过程,很多老科学家深受感染也时有收获。“中国(zhōngguó)稀土之父”徐光宪院士说:“她们往往早上来,工作(gōngzuò)到(dào)中午,出去简单(jiǎndān)午餐后又来工作。请她们在我家便餐,总是辞谢。她们辛劳勤奋的敬业精神使我深受感动。”徐院士觉得(juéde),采集小组整理的好多资料比自己知道的还要详尽,甚至激活了他一些模糊的回忆。
能参与这项“挖矿(wākuàng)”行动,成为众多采集人员宝贵的人生财富。
现就职于中国科协科学技术传播中心、持续参与采集工作十几年的(de)高文静至今仍清晰记得,2011年冬春交际的时节,他们到医院看望材料科学家颜鸣皋院士。颜院士已病重在床(chuáng),却硬要扶着助行器站起来(qǐlái),热情而庄重地跟(gēn)每个人握手。
“上世纪50年代,颜院士从美国辗转回国,带回的只有两箱在耶鲁大学学习期间的金属物理学笔记……”看着(kànzhe)一件件70多年前的物品,时光仿佛(fǎngfú)倒流;一个个当年场景在他的口述(kǒushù)、照片中重现。
“我们始终(shǐzhōng)有这样一种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,通过采集工程,为(wèi)科学家立传、为科技界立心、为民族和国家铸魂!”高文静说。
这样的(de)故事还有很多,通过对科学家进行口述访谈,并系统收集他们散存于各处的学术成长资料(zīliào),采集工程力争把反映(fǎnyìng)科学家学术成长经历的重要资料留存下来。
高文静还介绍了另一位“采集同仁”——来自北京应用物理与计算数学研究所的吴明静(míngjìng),她前后14年出版了《隐身为国铸核弹——于敏》《核以卫国——胡思得传(déchuán)》等4本传记(zhuànjì),每次给新的采集小组(xiǎozǔ)做培训和分享时,总会讲起“一张照片的故事”。
吴明静(míngjìng)负责采集的核武器工程专家、中国工程院院士胡思得,曾(céng)与“两弹一星”元勋邓稼先(dèngjiàxiān)密切合作多年。在一次电视台的采访中,胡院士回忆了与邓稼先一起工作、学习的许多往事,当(dāng)记者要一张他与邓稼先的合影时,胡院士沉默了,他收敛了笑容,遗憾地呐呐道:“没有,我(wǒ)没有与老邓单独合过影。”
在几十年的时间里,与(yǔ)自己敬重的师长一起亲密无间(qīnmìwújiàn)地(dì)学习(xuéxí)、工作,居然没有留下一张两人的合影。“但是,我理解。”吴明静在一篇采集手记中写道,“不仅因为他们从事的是高度涉密的工作,更因为某种习惯。这种低调的谦逊不是某一个人的特质,更像是核武器研制集体(jítǐ)的‘通识’——做民族脊梁,沉默中夯实基石。”
“终于有一天,胡院士小心翼翼地翻出一张黑白照片给我看,那是一张邓稼先同志追悼会的照片,国旗(guóqí)覆盖住邓老辛劳的躯体(qūtǐ),胡院士垂头凝视着(níngshìzhe)自己敬重的师长,仿佛舍不得作最后的告别。‘这不能算是合影吧?可是我跟老邓……也只有这么一张照片!’”吴明静说(shuō),这是(zhèshì)值得载入国史的真实故事。
“采集工程(gōngchéng)不仅是了解(liǎojiě)我国核武器发展史的(de)‘近道’,也是磨砺思想、锻炼文笔的‘顺风车’。”跟付出相比,吴明静更感谢采集工程丰富了自己的人生,虽然辛苦但很值得。
在采集过程中,工作(gōngzuò)人员时时被老科学家们求真务实、爱国奉献的(de)精神感动着。许多参与者都向记者表示:如果只当作一份工作的话,整天跟这些冷冰冰的资料打交道,可能会(huì)觉得枯燥;但如果你走进这些资料,就会感到炽热滚烫的情感(qínggǎn);它们不仅仅是记录共和国科技(kējì)发展的档案,更是追寻科学家们精彩人生的印迹。
采集工程中一些“意想不到”的片段,成为孟令耘脑海中(nǎohǎizhōng)挥之不去(huīzhībùqù)的场景:
1950年和邓稼先一同乘坐“威尔逊(wēiěrxùn)总统号”回国的微生物生化和分子遗传学家沈善炯院士,让中国成为世界第四个金霉素量产国,彻底打破了美国(měiguó)对抗生素(kàngshēngsù)的垄断。沈院士接受采集时已经偏瘫,好多事都记不清了,当被问到(wèndào)在(zài)美研究已上(shàng)轨道,为什么选择历尽艰辛回国时,“老先生沉默了挺长时间,然后用他发音已经很不清楚的上海腔给我们唱起了‘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……’”孟令耘说,“那一代老科学家的家国情怀(qínghuái),是刻在骨子里、融入基因中的。”
采集工作2010年正式启动,第一年组建了52个(gè)采集小组,主要面向(miànxiàng)年龄在80岁以上(yǐshàng)、学术成长经历丰富的两院院士,以及在我国科技事业发展中做出突出贡献的老科技工作者。
采集工程(gōngchéng)最初只是想抢救老科学家的资料,但在采集过程中,思路却逐渐清晰:收集上来的大量资料,不仅撑得起一座博物馆,从中解读(jiědú)出的科学家身上蕴含的精神特质,同样值得提炼和推广(tuīguǎng)。2018年,中国科协组织力量开始(kāishǐ)“凝练科学家精神”。
但也有不同意见:有了“科学精神(jīngshén)”,还有必要(bìyào)再搞个“科学家精神”吗?
经反复讨论,大家认识渐趋一致:“科学精神(jīngshén)”是科研人员普遍具备的价值观,但“科学家(kēxuéjiā)精神”是中国科学家身上表现突出甚至是独有的特质(tèzhì),比如爱国、奉献、育人等。最后和科技部关于(guānyú)加强作风学风建设的报告有机整合,上报中央。
2019年6月(yuè),中共中央办公厅、国务院办公厅印发《关于进一步弘扬科学家精神(jīngshén)加强作风和学风建设的意见》,对“科学家精神”作出全面(quánmiàn)概括。
2020年9月11日,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主持召开科学家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时指出:“科学成就离不开精神支撑。科学家精神是(shì)科技工作者在长期科学实践中积累(jīlěi)的宝贵(bǎoguì)精神财富。”
2021年9月,“科学家精神(jīngshén)”被(bèi)纳入第一批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。
在(zài)科学家博物馆的主展厅内,“科学家精神(jīngshén)”被大写在一整面展板上:胸怀祖国、服务人民的爱国精神,勇攀高峰(yǒngpāngāofēng)、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,追求真理、严谨治学的求实精神,淡泊名利、潜心研究的奉献精神,集智攻关、团结协作(xiézuò)的协同精神,甘为人梯(réntī)、奖掖后学的育人精神。
在(zài)两办印发的意见中,还明确提出了(le)“建设科学家博物馆,探索在国家和地方博物馆中增加反映科技进步的相关展项,依托科技馆(kējìguǎn)、国家重点实验室、重大(zhòngdà)科技工程纪念馆(遗迹)等设施建设一批科学家精神教育基地”等要求。
2024年5月30日,在第八个全国科技工作者(gōngzuòzhě)日,中国科学家博物馆正式开馆。它围绕采集史料(shǐliào)、收藏史料、学术研究、展览展示、教育教学、文化宣传等6项职能开展工作,并组织(zǔzhī)带动(dàidòng)全国科学家精神教育基地和相关教育科研机构,建立了全国科学家博物馆联合体。
这让曾向很多老科学家及家属承诺“给(gěi)资料找个好归宿”的(de)张藜松了一口气,“这些珍贵(zhēnguì)史料,不仅仅是老科学家们个人学术生涯的历史记录,更是相关领域近百年来在中国发轫、发展的真实写照”。
张藜还在北大开设了“共和国(gònghéguó)科技史研究(yánjiū)专题”课程,和采集工程结合起来,希望学生们通过参观博物馆、整理资料,学会(xuéhuì)分析解读中国现当代科技发展的历史。令她欣慰的是,有些学生的研究方向,已经做(zuò)得非常前沿了。
在博物馆展厅的留言簿上(shàng),有很多或稚嫩或雄劲的笔迹:
“原来科学这么有趣,我要好好学习,以后也像你们(nǐmen)一样,让(ràng)世界变得更神奇!”
“进入展馆听到钱学森院士讲(jiǎng)的一句话:‘外国人搞得,难道我们中国人不能搞?’正是有像钱老一样的科学家们一代一代的努力(nǔlì),才(cái)有了我们的强大。愿祖国繁荣昌盛!”
“在(zài)科学上没有平坦的道路,只有不畏(bùwèi)劳苦沿着陡峭山路攀登的人。”
“我们是站在巨人肩膀(jiānbǎng)上的一代人,吾辈当自强,定不负(bùfù)先生所望!”
令所有采集工程参与者倍感欣慰也足以自豪的是,他们的付出得到了(le)远超预想的回报(huíbào)。
很多资料具有极高的(de)史料价值和学术价值,比如科学家(kēxuéjiā)博物馆正在展出的地质学家谢家荣部分“简陋”的笔记本:十几个本子大小不等(dàxiǎobùděng)、封面(fēngmiàn)各异,甚至有一个贴着“1941年”标签的本子,就是用麻绳装订(zhuāngdìng)起来的一沓纸,已经泛黄(fànhuáng)的纸上密密麻麻记满了中英文混杂的小字,还依稀能看到(kàndào)背面透过来的字迹。这些1923-1949年间的工作笔记,记录了中国地质学事业乃至中国科学事业发展中的很多关键事件。
更不要说远远(yuǎnyuǎn)早于实体馆(guǎn)“开放”的(de)网上展厅。在中国科学家博物馆学术版网页(wǎngyè)上,由采集资料形成的纵深研究已有400余项:《童秉纲与中国生物运动力学的开拓》《陆埮:仰望星空、脚踏实地》《亲历者眼里的钱塘江防治往事——杨永楚访谈录(fǎngtánlù)》……馆藏资料已向社会开放,经过申请即可无偿查询。
采集成果的线下推广同样持续(chíxù)多年。自2013年“科技梦·中国梦——中国现代科学家(kēxuéjiā)主题展”首次亮相国博以来,采集工程先后组织策划了(le)“众心向党·自立自强——党领导下的科学家”等系列(xìliè)主题展览和全国巡展160余场,覆盖所有省(区、市)和港澳地区。只不过,看展(kànzhǎn)的观众可能想象不到这些展项背后的“国家工程”。
2023年,在采集工程的支持下,《共和国脊梁·科学家绘本丛书》出版。韩启德院士说(shuō):“绘本以适合儿童的故事内容(nèiróng)和绘画形式彰显科学家精神,融学术性(xuéshùxìng)、科学性和艺术性于一体,是近年来看到的最好(zuìhǎo)的儿童励志读物。”
随着采集工作的开展,影响范围持续扩大,很多高校、科研单位和机构也加入了保护老科学家历史资料的队伍中。“这是采集工程(gōngchéng)一个无形的影响力。我(wǒ)相信(xiāngxìn),如果所有的机构和相关人员都(dōu)能有这种保存历史记忆、保存科技界记忆并且(bìngqiě)共享出来的意识,采集工程的初心就实现了。”张藜说。
在第九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到来之际,第十四次中国公民科学(kēxué)(kēxué)素质抽样调查结果显示,2024年我国具备科学素质的公民比例达到15.37%;基本具备科学素质的公民比例为(wèi)44.07%,人口规模达4.4亿,为国家创新发展(fāzhǎn)进一步夯实劳动力基础。
“科学史是一个非常好的通识教育抓手,采集工程通过梳理历史发展的过程,对公民科学素质提升、价值观塑造,将起到一份不可替代的作用。”张藜说,“科技界前辈智慧与(yǔ)品格的结晶,可以启发(qǐfā)年轻一代(niánqīngyídài)崇敬(chóngjìng)科学家,推动科学领域(lǐngyù)的突破与创新,这与新质生产力培养的宗旨高度契合。”
和中国科技馆一路之隔的中国科学家博物馆(bówùguǎn)。新华每日电讯记者李牧鸣摄(shè)修史立典
“你知道吗?1999年我国隆重表彰的‘两弹一星’元勋有23位,可当年参与‘两弹一星’工程的科技工作者总共(zǒnggòng)有多少人(rén)?”中国科学家博物馆副馆长孟令耘(mènglìngyún)一下子问住了记者。
“据我们了解,光中国科学院系统参与的就超过1.7万人(wànrén)!但即使这(zhè)23位功勋科学家,大家(dàjiā)熟知的可能也不超过五六人。”孟令耘说。
的(de)确,因为资料保存不够、挖掘宣传不多,很多参与“两弹一星”工程的科技工作者没有留下只言片语甚至姓名(xìngmíng),能(néng)让后来者了解他们所作出的重要(zhòngyào)贡献。这,就是启动挖掘共和国“国家宝藏”工程的初衷。
在中国科学家博物馆三层(sāncéng)最(zuì)不起眼的一隅,“藏”着撑起(chēngqǐ)这座博物馆的庞大工程——“老科学家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程”(以下简称采集工程)。
这个(zhègè)(gè)看不见“热火朝天施工场面”的(de)大国工程,2009年经(niánjīng)国务院批准,由中国科协联合中组部等11个部委共同组织实施。15年来,已先后(xiānhòu)启动700多位(duōwèi)科学家(kēxuéjiā)的资料采集工作,获得实物原件15.9万件、数字化资料45.6万件、视频资料50.3万分钟、音频资料59.6万分钟,涵盖了中国科学家的书信、手稿、科学仪器、著作、音视频和记录中国科技发展重大事件的相关文物、文献等珍贵史料。
“这个‘工程’的(de)启动既是酝酿已久,也是机缘巧合(jīyuánqiǎohé)。”从立项到跟进,直至现在都一直参与其中的孟令耘回忆。
2009年5月,中国科协对(duì)两院院士(yuànshì)年龄情况进行了一次摸底调查。结果显示,当时中科院院士在世687人,平均年龄74.8岁(suì);工程院院士在世712人,平均年龄73.5岁;每年去世的院士在20人左右,平均每个(měigè)月就有两位院士离世。
老科学家是共和国建设的(de)重要参与者,是中国现当代科技发展的亲历者和见证者,他们的学术成长历程本身就是科技史(kējìshǐ)的重要组成部分。每位老科学家的离世都是其所在领域(lǐngyù)的重大损失,而相关(xiāngguān)资料的散失也是科技史研究的缺憾。
时任中国科协调研宣传部部长的王春法(wángchūnfǎ)提出一个想法:老一辈科学家很多已是90多岁高龄,如果再不(bù)及时抢救发掘他们的珍贵资料,后人研究共和国科技史时,比如某个决策是如何做出的,哪些人在(zài)关键节点发挥了什么作用,很多细节就湮没在历史(lìshǐ)的长河里了。
说干就干,王春法组织起草了一篇题为《老科学家学术(xuéshù)成长历史资料亟待抢救》的专题调研报告上报国务院(guówùyuàn),很快获批实施。采集工程2009年(nián)当年即拉开序幕。
如今(rújīn),这份(zhèfèn)触发共和国科技史修史工程的三千字报告,首页复印件就静静躺在博物馆三层的展板上,仿佛是带着我们穿越(chuānyuè)“时空裂隙”的“月光宝盒”。
可是资料由谁采集?怎么采集?如何保存?没有先例可循(kěxún)。
这是一项庞大复杂的(de)系统工程。孟令耘介绍,团队组织了科技史、图书馆、科技政策等方面(fāngmiàn)的专家,用(yòng)5个月的时间讨论(tǎolùn)研究出17项采集工程的标准、流程、规范等制度文件,包括怎么组建采集小组,怎么培训,采集到的资料怎么归档、编目,音视频使用什么(shénme)标准、格式,整理出来的资料怎么保存、利用,以及知识产权等问题。文件经2017年再次修订,现已成为国内(guónèi)人物,特别(tèbié)是科技人物信息采集业内公认的标准和流程。
按照这个标准和流程(liúchéng),每个采集小组对应(duìyìng)一位老科学家,小组人员(rényuán)搭配(dāpèi)科学合理:要有老科学家身边比较(bǐjiào)亲近的人,比如亲属、秘书或者学生,方便沟通和获取资料;必须有科技史方面的专家,对资料的科学性进行审定;还要有档案专家,对资料进行编目和规范整理;以及音视频拍摄人员等。
采集的最后成果,要形成一份15万字左右的学术性研究报告。而现已正式出版的180多部传记(zhuànjì)丛书,均成为记录(jìlù)共和国各个学科、各门工程技术发展历程的基础(jīchǔ)文献。
在博物馆(bówùguǎn)“采集工程”展厅,一整面墙的书架上,已出版的科学家传记静待读者(dúzhě)。与之遥相呼应,这套丛书也正摆在中科院图书馆“科技自立自强”专题文献(wénxiàn)展的醒目位置。
“这一丰富而庞大的学术成长(chéngzhǎng)资料库,有助于研究者(yánjiūzhě)厘清中国(zhōngguó)科技界的学术传承脉络,是(shì)共和国科技史的宝贵财富。”北京大学科学技术(kēxuéjìshù)与医学史系主任张藜是采集(cǎijí)工程首席科学家,“陪伴”采集工程15年的她,一度放下自己的学术研究,一个个地打电话,一家家地上门拜访,一次次地向老科学家和家属们保证:国家一定会好好保管捐赠的实物原件,一定会建一个平台永久珍藏。
“就是这样琐碎(suǒsuì)地收集、细致地整理、精心地挖掘,目前共发动全国500多家单位参与,超过(chāoguò)5000名采集人员投身(tóushēn)其中,接续15年的努力,才有今天的成果。”孟令耘说。
孟令耘向记者讲述了已于(yǐyú)2020年去世的专家组成员樊洪业先生的故事。他是中国近现代科学史方面的大家,曾花费十几年时间整理编撰了24卷《竺可桢全集(quánjí)》。樊洪业陪伴采集(cǎijí)工程(gōngchéng)整整十年,在每一次采集小组的评审会上,总是提出(tíchū)尖锐但极其中肯的修改意见。他是“采集工程最年长的志愿者”。
“在生命的最后几年,他(tā)几近失明,还是坚持把装有手稿资料的笔记本电脑拿到跟前,调大字号逐字逐句审看,让我们非常感动。正因为有一批把这项(zhèxiàng)工作(gōngzuò)作为毕生事业追求的专家,才使采集工程15年来保持一贯的高(gāo)学术水准。”孟令耘说。
采集工程也是一个“双向奔赴(bēnfù)”的过程,很多老科学家深受感染也时有收获。“中国(zhōngguó)稀土之父”徐光宪院士说:“她们往往早上来,工作(gōngzuò)到(dào)中午,出去简单(jiǎndān)午餐后又来工作。请她们在我家便餐,总是辞谢。她们辛劳勤奋的敬业精神使我深受感动。”徐院士觉得(juéde),采集小组整理的好多资料比自己知道的还要详尽,甚至激活了他一些模糊的回忆。
能参与这项“挖矿(wākuàng)”行动,成为众多采集人员宝贵的人生财富。
现就职于中国科协科学技术传播中心、持续参与采集工作十几年的(de)高文静至今仍清晰记得,2011年冬春交际的时节,他们到医院看望材料科学家颜鸣皋院士。颜院士已病重在床(chuáng),却硬要扶着助行器站起来(qǐlái),热情而庄重地跟(gēn)每个人握手。
“上世纪50年代,颜院士从美国辗转回国,带回的只有两箱在耶鲁大学学习期间的金属物理学笔记……”看着(kànzhe)一件件70多年前的物品,时光仿佛(fǎngfú)倒流;一个个当年场景在他的口述(kǒushù)、照片中重现。
“我们始终(shǐzhōng)有这样一种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,通过采集工程,为(wèi)科学家立传、为科技界立心、为民族和国家铸魂!”高文静说。
这样的(de)故事还有很多,通过对科学家进行口述访谈,并系统收集他们散存于各处的学术成长资料(zīliào),采集工程力争把反映(fǎnyìng)科学家学术成长经历的重要资料留存下来。
高文静还介绍了另一位“采集同仁”——来自北京应用物理与计算数学研究所的吴明静(míngjìng),她前后14年出版了《隐身为国铸核弹——于敏》《核以卫国——胡思得传(déchuán)》等4本传记(zhuànjì),每次给新的采集小组(xiǎozǔ)做培训和分享时,总会讲起“一张照片的故事”。
吴明静(míngjìng)负责采集的核武器工程专家、中国工程院院士胡思得,曾(céng)与“两弹一星”元勋邓稼先(dèngjiàxiān)密切合作多年。在一次电视台的采访中,胡院士回忆了与邓稼先一起工作、学习的许多往事,当(dāng)记者要一张他与邓稼先的合影时,胡院士沉默了,他收敛了笑容,遗憾地呐呐道:“没有,我(wǒ)没有与老邓单独合过影。”
在几十年的时间里,与(yǔ)自己敬重的师长一起亲密无间(qīnmìwújiàn)地(dì)学习(xuéxí)、工作,居然没有留下一张两人的合影。“但是,我理解。”吴明静在一篇采集手记中写道,“不仅因为他们从事的是高度涉密的工作,更因为某种习惯。这种低调的谦逊不是某一个人的特质,更像是核武器研制集体(jítǐ)的‘通识’——做民族脊梁,沉默中夯实基石。”
“终于有一天,胡院士小心翼翼地翻出一张黑白照片给我看,那是一张邓稼先同志追悼会的照片,国旗(guóqí)覆盖住邓老辛劳的躯体(qūtǐ),胡院士垂头凝视着(níngshìzhe)自己敬重的师长,仿佛舍不得作最后的告别。‘这不能算是合影吧?可是我跟老邓……也只有这么一张照片!’”吴明静说(shuō),这是(zhèshì)值得载入国史的真实故事。
“采集工程(gōngchéng)不仅是了解(liǎojiě)我国核武器发展史的(de)‘近道’,也是磨砺思想、锻炼文笔的‘顺风车’。”跟付出相比,吴明静更感谢采集工程丰富了自己的人生,虽然辛苦但很值得。
在采集过程中,工作(gōngzuò)人员时时被老科学家们求真务实、爱国奉献的(de)精神感动着。许多参与者都向记者表示:如果只当作一份工作的话,整天跟这些冷冰冰的资料打交道,可能会(huì)觉得枯燥;但如果你走进这些资料,就会感到炽热滚烫的情感(qínggǎn);它们不仅仅是记录共和国科技(kējì)发展的档案,更是追寻科学家们精彩人生的印迹。
采集工程中一些“意想不到”的片段,成为孟令耘脑海中(nǎohǎizhōng)挥之不去(huīzhībùqù)的场景:
1950年和邓稼先一同乘坐“威尔逊(wēiěrxùn)总统号”回国的微生物生化和分子遗传学家沈善炯院士,让中国成为世界第四个金霉素量产国,彻底打破了美国(měiguó)对抗生素(kàngshēngsù)的垄断。沈院士接受采集时已经偏瘫,好多事都记不清了,当被问到(wèndào)在(zài)美研究已上(shàng)轨道,为什么选择历尽艰辛回国时,“老先生沉默了挺长时间,然后用他发音已经很不清楚的上海腔给我们唱起了‘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……’”孟令耘说,“那一代老科学家的家国情怀(qínghuái),是刻在骨子里、融入基因中的。”
采集工作2010年正式启动,第一年组建了52个(gè)采集小组,主要面向(miànxiàng)年龄在80岁以上(yǐshàng)、学术成长经历丰富的两院院士,以及在我国科技事业发展中做出突出贡献的老科技工作者。
采集工程(gōngchéng)最初只是想抢救老科学家的资料,但在采集过程中,思路却逐渐清晰:收集上来的大量资料,不仅撑得起一座博物馆,从中解读(jiědú)出的科学家身上蕴含的精神特质,同样值得提炼和推广(tuīguǎng)。2018年,中国科协组织力量开始(kāishǐ)“凝练科学家精神”。
但也有不同意见:有了“科学精神(jīngshén)”,还有必要(bìyào)再搞个“科学家精神”吗?
经反复讨论,大家认识渐趋一致:“科学精神(jīngshén)”是科研人员普遍具备的价值观,但“科学家(kēxuéjiā)精神”是中国科学家身上表现突出甚至是独有的特质(tèzhì),比如爱国、奉献、育人等。最后和科技部关于(guānyú)加强作风学风建设的报告有机整合,上报中央。
2019年6月(yuè),中共中央办公厅、国务院办公厅印发《关于进一步弘扬科学家精神(jīngshén)加强作风和学风建设的意见》,对“科学家精神”作出全面(quánmiàn)概括。
2020年9月11日,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主持召开科学家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时指出:“科学成就离不开精神支撑。科学家精神是(shì)科技工作者在长期科学实践中积累(jīlěi)的宝贵(bǎoguì)精神财富。”
2021年9月,“科学家精神(jīngshén)”被(bèi)纳入第一批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。
在(zài)科学家博物馆的主展厅内,“科学家精神(jīngshén)”被大写在一整面展板上:胸怀祖国、服务人民的爱国精神,勇攀高峰(yǒngpāngāofēng)、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,追求真理、严谨治学的求实精神,淡泊名利、潜心研究的奉献精神,集智攻关、团结协作(xiézuò)的协同精神,甘为人梯(réntī)、奖掖后学的育人精神。
在(zài)两办印发的意见中,还明确提出了(le)“建设科学家博物馆,探索在国家和地方博物馆中增加反映科技进步的相关展项,依托科技馆(kējìguǎn)、国家重点实验室、重大(zhòngdà)科技工程纪念馆(遗迹)等设施建设一批科学家精神教育基地”等要求。
2024年5月30日,在第八个全国科技工作者(gōngzuòzhě)日,中国科学家博物馆正式开馆。它围绕采集史料(shǐliào)、收藏史料、学术研究、展览展示、教育教学、文化宣传等6项职能开展工作,并组织(zǔzhī)带动(dàidòng)全国科学家精神教育基地和相关教育科研机构,建立了全国科学家博物馆联合体。
这让曾向很多老科学家及家属承诺“给(gěi)资料找个好归宿”的(de)张藜松了一口气,“这些珍贵(zhēnguì)史料,不仅仅是老科学家们个人学术生涯的历史记录,更是相关领域近百年来在中国发轫、发展的真实写照”。
张藜还在北大开设了“共和国(gònghéguó)科技史研究(yánjiū)专题”课程,和采集工程结合起来,希望学生们通过参观博物馆、整理资料,学会(xuéhuì)分析解读中国现当代科技发展的历史。令她欣慰的是,有些学生的研究方向,已经做(zuò)得非常前沿了。
在博物馆展厅的留言簿上(shàng),有很多或稚嫩或雄劲的笔迹:
“原来科学这么有趣,我要好好学习,以后也像你们(nǐmen)一样,让(ràng)世界变得更神奇!”
“进入展馆听到钱学森院士讲(jiǎng)的一句话:‘外国人搞得,难道我们中国人不能搞?’正是有像钱老一样的科学家们一代一代的努力(nǔlì),才(cái)有了我们的强大。愿祖国繁荣昌盛!”
“在(zài)科学上没有平坦的道路,只有不畏(bùwèi)劳苦沿着陡峭山路攀登的人。”
“我们是站在巨人肩膀(jiānbǎng)上的一代人,吾辈当自强,定不负(bùfù)先生所望!”
令所有采集工程参与者倍感欣慰也足以自豪的是,他们的付出得到了(le)远超预想的回报(huíbào)。
很多资料具有极高的(de)史料价值和学术价值,比如科学家(kēxuéjiā)博物馆正在展出的地质学家谢家荣部分“简陋”的笔记本:十几个本子大小不等(dàxiǎobùděng)、封面(fēngmiàn)各异,甚至有一个贴着“1941年”标签的本子,就是用麻绳装订(zhuāngdìng)起来的一沓纸,已经泛黄(fànhuáng)的纸上密密麻麻记满了中英文混杂的小字,还依稀能看到(kàndào)背面透过来的字迹。这些1923-1949年间的工作笔记,记录了中国地质学事业乃至中国科学事业发展中的很多关键事件。
更不要说远远(yuǎnyuǎn)早于实体馆(guǎn)“开放”的(de)网上展厅。在中国科学家博物馆学术版网页(wǎngyè)上,由采集资料形成的纵深研究已有400余项:《童秉纲与中国生物运动力学的开拓》《陆埮:仰望星空、脚踏实地》《亲历者眼里的钱塘江防治往事——杨永楚访谈录(fǎngtánlù)》……馆藏资料已向社会开放,经过申请即可无偿查询。
采集成果的线下推广同样持续(chíxù)多年。自2013年“科技梦·中国梦——中国现代科学家(kēxuéjiā)主题展”首次亮相国博以来,采集工程先后组织策划了(le)“众心向党·自立自强——党领导下的科学家”等系列(xìliè)主题展览和全国巡展160余场,覆盖所有省(区、市)和港澳地区。只不过,看展(kànzhǎn)的观众可能想象不到这些展项背后的“国家工程”。
2023年,在采集工程的支持下,《共和国脊梁·科学家绘本丛书》出版。韩启德院士说(shuō):“绘本以适合儿童的故事内容(nèiróng)和绘画形式彰显科学家精神,融学术性(xuéshùxìng)、科学性和艺术性于一体,是近年来看到的最好(zuìhǎo)的儿童励志读物。”
随着采集工作的开展,影响范围持续扩大,很多高校、科研单位和机构也加入了保护老科学家历史资料的队伍中。“这是采集工程(gōngchéng)一个无形的影响力。我(wǒ)相信(xiāngxìn),如果所有的机构和相关人员都(dōu)能有这种保存历史记忆、保存科技界记忆并且(bìngqiě)共享出来的意识,采集工程的初心就实现了。”张藜说。
在第九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到来之际,第十四次中国公民科学(kēxué)(kēxué)素质抽样调查结果显示,2024年我国具备科学素质的公民比例达到15.37%;基本具备科学素质的公民比例为(wèi)44.07%,人口规模达4.4亿,为国家创新发展(fāzhǎn)进一步夯实劳动力基础。
“科学史是一个非常好的通识教育抓手,采集工程通过梳理历史发展的过程,对公民科学素质提升、价值观塑造,将起到一份不可替代的作用。”张藜说,“科技界前辈智慧与(yǔ)品格的结晶,可以启发(qǐfā)年轻一代(niánqīngyídài)崇敬(chóngjìng)科学家,推动科学领域(lǐngyù)的突破与创新,这与新质生产力培养的宗旨高度契合。”
新华社北京5月(yuè)30日电 5月30日,《新华每日电讯》发表题为《走进(zǒujìn)中国科学家博物馆感悟“科学家精神”》的报道。
“推开博物馆厚重的玻璃门,仿佛踏入一道(yīdào)时空裂隙。这里没有网红展(wǎnghóngzhǎn)的浮躁(fúzào)喧嚣,只有泛黄手稿上的墨迹沉默翻涌,沙盘剧场的风声低吟着戈壁往事,以及一群把名字刻进星河的人,用(yòng)一生写下的答案。”
网友“媛媛不圆”在社交媒体上的(de)这段笔记,击中了(le)记者心中最柔软的部分。我们都在一个春日(chūnrì)邂逅了一座让人激情澎湃的博物馆,在里面找到了共和国的“国家宝藏”。
这座博物馆(bówùguǎn)就是中国科学家博物馆。它位于北京城中轴线北端的奥林匹克中心区,与中国科学技术馆一街之隔、廊桥相连(xiānglián),是全世界首个以国家名义为科学家群体建立、弘扬科学家精神、打造(dǎzào)科技(kējì)工作者精神殿堂的博物馆。
走进(zǒujìn)7500平方米(píngfāngmǐ)的展厅,宛如踏入浩瀚无垠的时空长廊:李四光、竺可桢、钱学森、王淦昌(wánggànchāng)……这些熟悉的名字,如雷贯耳,他们的功业,国人早已耳熟能详。而更多的,是一个个有些陌生的名字,但无一例外,他们每个人,都(dōu)是一片星空中最为闪亮的那一颗。
 和中国科技馆一路之隔的中国科学家博物馆(bówùguǎn)。新华每日电讯记者李牧鸣摄(shè)修史立典
“你知道吗?1999年我国隆重表彰的‘两弹一星’元勋有23位,可当年参与‘两弹一星’工程的科技工作者总共(zǒnggòng)有多少人(rén)?”中国科学家博物馆副馆长孟令耘(mènglìngyún)一下子问住了记者。
“据我们了解,光中国科学院系统参与的就超过1.7万人(wànrén)!但即使这(zhè)23位功勋科学家,大家(dàjiā)熟知的可能也不超过五六人。”孟令耘说。
的(de)确,因为资料保存不够、挖掘宣传不多,很多参与“两弹一星”工程的科技工作者没有留下只言片语甚至姓名(xìngmíng),能(néng)让后来者了解他们所作出的重要(zhòngyào)贡献。这,就是启动挖掘共和国“国家宝藏”工程的初衷。
在中国科学家博物馆三层(sāncéng)最(zuì)不起眼的一隅,“藏”着撑起(chēngqǐ)这座博物馆的庞大工程——“老科学家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程”(以下简称采集工程)。
这个(zhègè)(gè)看不见“热火朝天施工场面”的(de)大国工程,2009年经(niánjīng)国务院批准,由中国科协联合中组部等11个部委共同组织实施。15年来,已先后(xiānhòu)启动700多位(duōwèi)科学家(kēxuéjiā)的资料采集工作,获得实物原件15.9万件、数字化资料45.6万件、视频资料50.3万分钟、音频资料59.6万分钟,涵盖了中国科学家的书信、手稿、科学仪器、著作、音视频和记录中国科技发展重大事件的相关文物、文献等珍贵史料。
“这个‘工程’的(de)启动既是酝酿已久,也是机缘巧合(jīyuánqiǎohé)。”从立项到跟进,直至现在都一直参与其中的孟令耘回忆。
2009年5月,中国科协对(duì)两院院士(yuànshì)年龄情况进行了一次摸底调查。结果显示,当时中科院院士在世687人,平均年龄74.8岁(suì);工程院院士在世712人,平均年龄73.5岁;每年去世的院士在20人左右,平均每个(měigè)月就有两位院士离世。
老科学家是共和国建设的(de)重要参与者,是中国现当代科技发展的亲历者和见证者,他们的学术成长历程本身就是科技史(kējìshǐ)的重要组成部分。每位老科学家的离世都是其所在领域(lǐngyù)的重大损失,而相关(xiāngguān)资料的散失也是科技史研究的缺憾。
时任中国科协调研宣传部部长的王春法(wángchūnfǎ)提出一个想法:老一辈科学家很多已是90多岁高龄,如果再不(bù)及时抢救发掘他们的珍贵资料,后人研究共和国科技史时,比如某个决策是如何做出的,哪些人在(zài)关键节点发挥了什么作用,很多细节就湮没在历史(lìshǐ)的长河里了。
说干就干,王春法组织起草了一篇题为《老科学家学术(xuéshù)成长历史资料亟待抢救》的专题调研报告上报国务院(guówùyuàn),很快获批实施。采集工程2009年(nián)当年即拉开序幕。
如今(rújīn),这份(zhèfèn)触发共和国科技史修史工程的三千字报告,首页复印件就静静躺在博物馆三层的展板上,仿佛是带着我们穿越(chuānyuè)“时空裂隙”的“月光宝盒”。
可是资料由谁采集?怎么采集?如何保存?没有先例可循(kěxún)。
这是一项庞大复杂的(de)系统工程。孟令耘介绍,团队组织了科技史、图书馆、科技政策等方面(fāngmiàn)的专家,用(yòng)5个月的时间讨论(tǎolùn)研究出17项采集工程的标准、流程、规范等制度文件,包括怎么组建采集小组,怎么培训,采集到的资料怎么归档、编目,音视频使用什么(shénme)标准、格式,整理出来的资料怎么保存、利用,以及知识产权等问题。文件经2017年再次修订,现已成为国内(guónèi)人物,特别(tèbié)是科技人物信息采集业内公认的标准和流程。
按照这个标准和流程(liúchéng),每个采集小组对应(duìyìng)一位老科学家,小组人员(rényuán)搭配(dāpèi)科学合理:要有老科学家身边比较(bǐjiào)亲近的人,比如亲属、秘书或者学生,方便沟通和获取资料;必须有科技史方面的专家,对资料的科学性进行审定;还要有档案专家,对资料进行编目和规范整理;以及音视频拍摄人员等。
采集的最后成果,要形成一份15万字左右的学术性研究报告。而现已正式出版的180多部传记(zhuànjì)丛书,均成为记录(jìlù)共和国各个学科、各门工程技术发展历程的基础(jīchǔ)文献。
在博物馆(bówùguǎn)“采集工程”展厅,一整面墙的书架上,已出版的科学家传记静待读者(dúzhě)。与之遥相呼应,这套丛书也正摆在中科院图书馆“科技自立自强”专题文献(wénxiàn)展的醒目位置。
“这一丰富而庞大的学术成长(chéngzhǎng)资料库,有助于研究者(yánjiūzhě)厘清中国(zhōngguó)科技界的学术传承脉络,是(shì)共和国科技史的宝贵财富。”北京大学科学技术(kēxuéjìshù)与医学史系主任张藜是采集(cǎijí)工程首席科学家,“陪伴”采集工程15年的她,一度放下自己的学术研究,一个个地打电话,一家家地上门拜访,一次次地向老科学家和家属们保证:国家一定会好好保管捐赠的实物原件,一定会建一个平台永久珍藏。
“就是这样琐碎(suǒsuì)地收集、细致地整理、精心地挖掘,目前共发动全国500多家单位参与,超过(chāoguò)5000名采集人员投身(tóushēn)其中,接续15年的努力,才有今天的成果。”孟令耘说。
孟令耘向记者讲述了已于(yǐyú)2020年去世的专家组成员樊洪业先生的故事。他是中国近现代科学史方面的大家,曾花费十几年时间整理编撰了24卷《竺可桢全集(quánjí)》。樊洪业陪伴采集(cǎijí)工程(gōngchéng)整整十年,在每一次采集小组的评审会上,总是提出(tíchū)尖锐但极其中肯的修改意见。他是“采集工程最年长的志愿者”。
“在生命的最后几年,他(tā)几近失明,还是坚持把装有手稿资料的笔记本电脑拿到跟前,调大字号逐字逐句审看,让我们非常感动。正因为有一批把这项(zhèxiàng)工作(gōngzuò)作为毕生事业追求的专家,才使采集工程15年来保持一贯的高(gāo)学术水准。”孟令耘说。
采集工程也是一个“双向奔赴(bēnfù)”的过程,很多老科学家深受感染也时有收获。“中国(zhōngguó)稀土之父”徐光宪院士说:“她们往往早上来,工作(gōngzuò)到(dào)中午,出去简单(jiǎndān)午餐后又来工作。请她们在我家便餐,总是辞谢。她们辛劳勤奋的敬业精神使我深受感动。”徐院士觉得(juéde),采集小组整理的好多资料比自己知道的还要详尽,甚至激活了他一些模糊的回忆。
能参与这项“挖矿(wākuàng)”行动,成为众多采集人员宝贵的人生财富。
现就职于中国科协科学技术传播中心、持续参与采集工作十几年的(de)高文静至今仍清晰记得,2011年冬春交际的时节,他们到医院看望材料科学家颜鸣皋院士。颜院士已病重在床(chuáng),却硬要扶着助行器站起来(qǐlái),热情而庄重地跟(gēn)每个人握手。
“上世纪50年代,颜院士从美国辗转回国,带回的只有两箱在耶鲁大学学习期间的金属物理学笔记……”看着(kànzhe)一件件70多年前的物品,时光仿佛(fǎngfú)倒流;一个个当年场景在他的口述(kǒushù)、照片中重现。
“我们始终(shǐzhōng)有这样一种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,通过采集工程,为(wèi)科学家立传、为科技界立心、为民族和国家铸魂!”高文静说。
这样的(de)故事还有很多,通过对科学家进行口述访谈,并系统收集他们散存于各处的学术成长资料(zīliào),采集工程力争把反映(fǎnyìng)科学家学术成长经历的重要资料留存下来。
高文静还介绍了另一位“采集同仁”——来自北京应用物理与计算数学研究所的吴明静(míngjìng),她前后14年出版了《隐身为国铸核弹——于敏》《核以卫国——胡思得传(déchuán)》等4本传记(zhuànjì),每次给新的采集小组(xiǎozǔ)做培训和分享时,总会讲起“一张照片的故事”。
吴明静(míngjìng)负责采集的核武器工程专家、中国工程院院士胡思得,曾(céng)与“两弹一星”元勋邓稼先(dèngjiàxiān)密切合作多年。在一次电视台的采访中,胡院士回忆了与邓稼先一起工作、学习的许多往事,当(dāng)记者要一张他与邓稼先的合影时,胡院士沉默了,他收敛了笑容,遗憾地呐呐道:“没有,我(wǒ)没有与老邓单独合过影。”
在几十年的时间里,与(yǔ)自己敬重的师长一起亲密无间(qīnmìwújiàn)地(dì)学习(xuéxí)、工作,居然没有留下一张两人的合影。“但是,我理解。”吴明静在一篇采集手记中写道,“不仅因为他们从事的是高度涉密的工作,更因为某种习惯。这种低调的谦逊不是某一个人的特质,更像是核武器研制集体(jítǐ)的‘通识’——做民族脊梁,沉默中夯实基石。”
“终于有一天,胡院士小心翼翼地翻出一张黑白照片给我看,那是一张邓稼先同志追悼会的照片,国旗(guóqí)覆盖住邓老辛劳的躯体(qūtǐ),胡院士垂头凝视着(níngshìzhe)自己敬重的师长,仿佛舍不得作最后的告别。‘这不能算是合影吧?可是我跟老邓……也只有这么一张照片!’”吴明静说(shuō),这是(zhèshì)值得载入国史的真实故事。
“采集工程(gōngchéng)不仅是了解(liǎojiě)我国核武器发展史的(de)‘近道’,也是磨砺思想、锻炼文笔的‘顺风车’。”跟付出相比,吴明静更感谢采集工程丰富了自己的人生,虽然辛苦但很值得。
在采集过程中,工作(gōngzuò)人员时时被老科学家们求真务实、爱国奉献的(de)精神感动着。许多参与者都向记者表示:如果只当作一份工作的话,整天跟这些冷冰冰的资料打交道,可能会(huì)觉得枯燥;但如果你走进这些资料,就会感到炽热滚烫的情感(qínggǎn);它们不仅仅是记录共和国科技(kējì)发展的档案,更是追寻科学家们精彩人生的印迹。
采集工程中一些“意想不到”的片段,成为孟令耘脑海中(nǎohǎizhōng)挥之不去(huīzhībùqù)的场景:
1950年和邓稼先一同乘坐“威尔逊(wēiěrxùn)总统号”回国的微生物生化和分子遗传学家沈善炯院士,让中国成为世界第四个金霉素量产国,彻底打破了美国(měiguó)对抗生素(kàngshēngsù)的垄断。沈院士接受采集时已经偏瘫,好多事都记不清了,当被问到(wèndào)在(zài)美研究已上(shàng)轨道,为什么选择历尽艰辛回国时,“老先生沉默了挺长时间,然后用他发音已经很不清楚的上海腔给我们唱起了‘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……’”孟令耘说,“那一代老科学家的家国情怀(qínghuái),是刻在骨子里、融入基因中的。”
采集工作2010年正式启动,第一年组建了52个(gè)采集小组,主要面向(miànxiàng)年龄在80岁以上(yǐshàng)、学术成长经历丰富的两院院士,以及在我国科技事业发展中做出突出贡献的老科技工作者。
采集工程(gōngchéng)最初只是想抢救老科学家的资料,但在采集过程中,思路却逐渐清晰:收集上来的大量资料,不仅撑得起一座博物馆,从中解读(jiědú)出的科学家身上蕴含的精神特质,同样值得提炼和推广(tuīguǎng)。2018年,中国科协组织力量开始(kāishǐ)“凝练科学家精神”。
但也有不同意见:有了“科学精神(jīngshén)”,还有必要(bìyào)再搞个“科学家精神”吗?
经反复讨论,大家认识渐趋一致:“科学精神(jīngshén)”是科研人员普遍具备的价值观,但“科学家(kēxuéjiā)精神”是中国科学家身上表现突出甚至是独有的特质(tèzhì),比如爱国、奉献、育人等。最后和科技部关于(guānyú)加强作风学风建设的报告有机整合,上报中央。
2019年6月(yuè),中共中央办公厅、国务院办公厅印发《关于进一步弘扬科学家精神(jīngshén)加强作风和学风建设的意见》,对“科学家精神”作出全面(quánmiàn)概括。
2020年9月11日,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主持召开科学家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时指出:“科学成就离不开精神支撑。科学家精神是(shì)科技工作者在长期科学实践中积累(jīlěi)的宝贵(bǎoguì)精神财富。”
2021年9月,“科学家精神(jīngshén)”被(bèi)纳入第一批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。
在(zài)科学家博物馆的主展厅内,“科学家精神(jīngshén)”被大写在一整面展板上:胸怀祖国、服务人民的爱国精神,勇攀高峰(yǒngpāngāofēng)、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,追求真理、严谨治学的求实精神,淡泊名利、潜心研究的奉献精神,集智攻关、团结协作(xiézuò)的协同精神,甘为人梯(réntī)、奖掖后学的育人精神。
在(zài)两办印发的意见中,还明确提出了(le)“建设科学家博物馆,探索在国家和地方博物馆中增加反映科技进步的相关展项,依托科技馆(kējìguǎn)、国家重点实验室、重大(zhòngdà)科技工程纪念馆(遗迹)等设施建设一批科学家精神教育基地”等要求。
2024年5月30日,在第八个全国科技工作者(gōngzuòzhě)日,中国科学家博物馆正式开馆。它围绕采集史料(shǐliào)、收藏史料、学术研究、展览展示、教育教学、文化宣传等6项职能开展工作,并组织(zǔzhī)带动(dàidòng)全国科学家精神教育基地和相关教育科研机构,建立了全国科学家博物馆联合体。
这让曾向很多老科学家及家属承诺“给(gěi)资料找个好归宿”的(de)张藜松了一口气,“这些珍贵(zhēnguì)史料,不仅仅是老科学家们个人学术生涯的历史记录,更是相关领域近百年来在中国发轫、发展的真实写照”。
张藜还在北大开设了“共和国(gònghéguó)科技史研究(yánjiū)专题”课程,和采集工程结合起来,希望学生们通过参观博物馆、整理资料,学会(xuéhuì)分析解读中国现当代科技发展的历史。令她欣慰的是,有些学生的研究方向,已经做(zuò)得非常前沿了。
在博物馆展厅的留言簿上(shàng),有很多或稚嫩或雄劲的笔迹:
“原来科学这么有趣,我要好好学习,以后也像你们(nǐmen)一样,让(ràng)世界变得更神奇!”
“进入展馆听到钱学森院士讲(jiǎng)的一句话:‘外国人搞得,难道我们中国人不能搞?’正是有像钱老一样的科学家们一代一代的努力(nǔlì),才(cái)有了我们的强大。愿祖国繁荣昌盛!”
“在(zài)科学上没有平坦的道路,只有不畏(bùwèi)劳苦沿着陡峭山路攀登的人。”
“我们是站在巨人肩膀(jiānbǎng)上的一代人,吾辈当自强,定不负(bùfù)先生所望!”
令所有采集工程参与者倍感欣慰也足以自豪的是,他们的付出得到了(le)远超预想的回报(huíbào)。
很多资料具有极高的(de)史料价值和学术价值,比如科学家(kēxuéjiā)博物馆正在展出的地质学家谢家荣部分“简陋”的笔记本:十几个本子大小不等(dàxiǎobùděng)、封面(fēngmiàn)各异,甚至有一个贴着“1941年”标签的本子,就是用麻绳装订(zhuāngdìng)起来的一沓纸,已经泛黄(fànhuáng)的纸上密密麻麻记满了中英文混杂的小字,还依稀能看到(kàndào)背面透过来的字迹。这些1923-1949年间的工作笔记,记录了中国地质学事业乃至中国科学事业发展中的很多关键事件。
更不要说远远(yuǎnyuǎn)早于实体馆(guǎn)“开放”的(de)网上展厅。在中国科学家博物馆学术版网页(wǎngyè)上,由采集资料形成的纵深研究已有400余项:《童秉纲与中国生物运动力学的开拓》《陆埮:仰望星空、脚踏实地》《亲历者眼里的钱塘江防治往事——杨永楚访谈录(fǎngtánlù)》……馆藏资料已向社会开放,经过申请即可无偿查询。
采集成果的线下推广同样持续(chíxù)多年。自2013年“科技梦·中国梦——中国现代科学家(kēxuéjiā)主题展”首次亮相国博以来,采集工程先后组织策划了(le)“众心向党·自立自强——党领导下的科学家”等系列(xìliè)主题展览和全国巡展160余场,覆盖所有省(区、市)和港澳地区。只不过,看展(kànzhǎn)的观众可能想象不到这些展项背后的“国家工程”。
2023年,在采集工程的支持下,《共和国脊梁·科学家绘本丛书》出版。韩启德院士说(shuō):“绘本以适合儿童的故事内容(nèiróng)和绘画形式彰显科学家精神,融学术性(xuéshùxìng)、科学性和艺术性于一体,是近年来看到的最好(zuìhǎo)的儿童励志读物。”
随着采集工作的开展,影响范围持续扩大,很多高校、科研单位和机构也加入了保护老科学家历史资料的队伍中。“这是采集工程(gōngchéng)一个无形的影响力。我(wǒ)相信(xiāngxìn),如果所有的机构和相关人员都(dōu)能有这种保存历史记忆、保存科技界记忆并且(bìngqiě)共享出来的意识,采集工程的初心就实现了。”张藜说。
在第九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到来之际,第十四次中国公民科学(kēxué)(kēxué)素质抽样调查结果显示,2024年我国具备科学素质的公民比例达到15.37%;基本具备科学素质的公民比例为(wèi)44.07%,人口规模达4.4亿,为国家创新发展(fāzhǎn)进一步夯实劳动力基础。
“科学史是一个非常好的通识教育抓手,采集工程通过梳理历史发展的过程,对公民科学素质提升、价值观塑造,将起到一份不可替代的作用。”张藜说,“科技界前辈智慧与(yǔ)品格的结晶,可以启发(qǐfā)年轻一代(niánqīngyídài)崇敬(chóngjìng)科学家,推动科学领域(lǐngyù)的突破与创新,这与新质生产力培养的宗旨高度契合。”
和中国科技馆一路之隔的中国科学家博物馆(bówùguǎn)。新华每日电讯记者李牧鸣摄(shè)修史立典
“你知道吗?1999年我国隆重表彰的‘两弹一星’元勋有23位,可当年参与‘两弹一星’工程的科技工作者总共(zǒnggòng)有多少人(rén)?”中国科学家博物馆副馆长孟令耘(mènglìngyún)一下子问住了记者。
“据我们了解,光中国科学院系统参与的就超过1.7万人(wànrén)!但即使这(zhè)23位功勋科学家,大家(dàjiā)熟知的可能也不超过五六人。”孟令耘说。
的(de)确,因为资料保存不够、挖掘宣传不多,很多参与“两弹一星”工程的科技工作者没有留下只言片语甚至姓名(xìngmíng),能(néng)让后来者了解他们所作出的重要(zhòngyào)贡献。这,就是启动挖掘共和国“国家宝藏”工程的初衷。
在中国科学家博物馆三层(sāncéng)最(zuì)不起眼的一隅,“藏”着撑起(chēngqǐ)这座博物馆的庞大工程——“老科学家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程”(以下简称采集工程)。
这个(zhègè)(gè)看不见“热火朝天施工场面”的(de)大国工程,2009年经(niánjīng)国务院批准,由中国科协联合中组部等11个部委共同组织实施。15年来,已先后(xiānhòu)启动700多位(duōwèi)科学家(kēxuéjiā)的资料采集工作,获得实物原件15.9万件、数字化资料45.6万件、视频资料50.3万分钟、音频资料59.6万分钟,涵盖了中国科学家的书信、手稿、科学仪器、著作、音视频和记录中国科技发展重大事件的相关文物、文献等珍贵史料。
“这个‘工程’的(de)启动既是酝酿已久,也是机缘巧合(jīyuánqiǎohé)。”从立项到跟进,直至现在都一直参与其中的孟令耘回忆。
2009年5月,中国科协对(duì)两院院士(yuànshì)年龄情况进行了一次摸底调查。结果显示,当时中科院院士在世687人,平均年龄74.8岁(suì);工程院院士在世712人,平均年龄73.5岁;每年去世的院士在20人左右,平均每个(měigè)月就有两位院士离世。
老科学家是共和国建设的(de)重要参与者,是中国现当代科技发展的亲历者和见证者,他们的学术成长历程本身就是科技史(kējìshǐ)的重要组成部分。每位老科学家的离世都是其所在领域(lǐngyù)的重大损失,而相关(xiāngguān)资料的散失也是科技史研究的缺憾。
时任中国科协调研宣传部部长的王春法(wángchūnfǎ)提出一个想法:老一辈科学家很多已是90多岁高龄,如果再不(bù)及时抢救发掘他们的珍贵资料,后人研究共和国科技史时,比如某个决策是如何做出的,哪些人在(zài)关键节点发挥了什么作用,很多细节就湮没在历史(lìshǐ)的长河里了。
说干就干,王春法组织起草了一篇题为《老科学家学术(xuéshù)成长历史资料亟待抢救》的专题调研报告上报国务院(guówùyuàn),很快获批实施。采集工程2009年(nián)当年即拉开序幕。
如今(rújīn),这份(zhèfèn)触发共和国科技史修史工程的三千字报告,首页复印件就静静躺在博物馆三层的展板上,仿佛是带着我们穿越(chuānyuè)“时空裂隙”的“月光宝盒”。
可是资料由谁采集?怎么采集?如何保存?没有先例可循(kěxún)。
这是一项庞大复杂的(de)系统工程。孟令耘介绍,团队组织了科技史、图书馆、科技政策等方面(fāngmiàn)的专家,用(yòng)5个月的时间讨论(tǎolùn)研究出17项采集工程的标准、流程、规范等制度文件,包括怎么组建采集小组,怎么培训,采集到的资料怎么归档、编目,音视频使用什么(shénme)标准、格式,整理出来的资料怎么保存、利用,以及知识产权等问题。文件经2017年再次修订,现已成为国内(guónèi)人物,特别(tèbié)是科技人物信息采集业内公认的标准和流程。
按照这个标准和流程(liúchéng),每个采集小组对应(duìyìng)一位老科学家,小组人员(rényuán)搭配(dāpèi)科学合理:要有老科学家身边比较(bǐjiào)亲近的人,比如亲属、秘书或者学生,方便沟通和获取资料;必须有科技史方面的专家,对资料的科学性进行审定;还要有档案专家,对资料进行编目和规范整理;以及音视频拍摄人员等。
采集的最后成果,要形成一份15万字左右的学术性研究报告。而现已正式出版的180多部传记(zhuànjì)丛书,均成为记录(jìlù)共和国各个学科、各门工程技术发展历程的基础(jīchǔ)文献。
在博物馆(bówùguǎn)“采集工程”展厅,一整面墙的书架上,已出版的科学家传记静待读者(dúzhě)。与之遥相呼应,这套丛书也正摆在中科院图书馆“科技自立自强”专题文献(wénxiàn)展的醒目位置。
“这一丰富而庞大的学术成长(chéngzhǎng)资料库,有助于研究者(yánjiūzhě)厘清中国(zhōngguó)科技界的学术传承脉络,是(shì)共和国科技史的宝贵财富。”北京大学科学技术(kēxuéjìshù)与医学史系主任张藜是采集(cǎijí)工程首席科学家,“陪伴”采集工程15年的她,一度放下自己的学术研究,一个个地打电话,一家家地上门拜访,一次次地向老科学家和家属们保证:国家一定会好好保管捐赠的实物原件,一定会建一个平台永久珍藏。
“就是这样琐碎(suǒsuì)地收集、细致地整理、精心地挖掘,目前共发动全国500多家单位参与,超过(chāoguò)5000名采集人员投身(tóushēn)其中,接续15年的努力,才有今天的成果。”孟令耘说。
孟令耘向记者讲述了已于(yǐyú)2020年去世的专家组成员樊洪业先生的故事。他是中国近现代科学史方面的大家,曾花费十几年时间整理编撰了24卷《竺可桢全集(quánjí)》。樊洪业陪伴采集(cǎijí)工程(gōngchéng)整整十年,在每一次采集小组的评审会上,总是提出(tíchū)尖锐但极其中肯的修改意见。他是“采集工程最年长的志愿者”。
“在生命的最后几年,他(tā)几近失明,还是坚持把装有手稿资料的笔记本电脑拿到跟前,调大字号逐字逐句审看,让我们非常感动。正因为有一批把这项(zhèxiàng)工作(gōngzuò)作为毕生事业追求的专家,才使采集工程15年来保持一贯的高(gāo)学术水准。”孟令耘说。
采集工程也是一个“双向奔赴(bēnfù)”的过程,很多老科学家深受感染也时有收获。“中国(zhōngguó)稀土之父”徐光宪院士说:“她们往往早上来,工作(gōngzuò)到(dào)中午,出去简单(jiǎndān)午餐后又来工作。请她们在我家便餐,总是辞谢。她们辛劳勤奋的敬业精神使我深受感动。”徐院士觉得(juéde),采集小组整理的好多资料比自己知道的还要详尽,甚至激活了他一些模糊的回忆。
能参与这项“挖矿(wākuàng)”行动,成为众多采集人员宝贵的人生财富。
现就职于中国科协科学技术传播中心、持续参与采集工作十几年的(de)高文静至今仍清晰记得,2011年冬春交际的时节,他们到医院看望材料科学家颜鸣皋院士。颜院士已病重在床(chuáng),却硬要扶着助行器站起来(qǐlái),热情而庄重地跟(gēn)每个人握手。
“上世纪50年代,颜院士从美国辗转回国,带回的只有两箱在耶鲁大学学习期间的金属物理学笔记……”看着(kànzhe)一件件70多年前的物品,时光仿佛(fǎngfú)倒流;一个个当年场景在他的口述(kǒushù)、照片中重现。
“我们始终(shǐzhōng)有这样一种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,通过采集工程,为(wèi)科学家立传、为科技界立心、为民族和国家铸魂!”高文静说。
这样的(de)故事还有很多,通过对科学家进行口述访谈,并系统收集他们散存于各处的学术成长资料(zīliào),采集工程力争把反映(fǎnyìng)科学家学术成长经历的重要资料留存下来。
高文静还介绍了另一位“采集同仁”——来自北京应用物理与计算数学研究所的吴明静(míngjìng),她前后14年出版了《隐身为国铸核弹——于敏》《核以卫国——胡思得传(déchuán)》等4本传记(zhuànjì),每次给新的采集小组(xiǎozǔ)做培训和分享时,总会讲起“一张照片的故事”。
吴明静(míngjìng)负责采集的核武器工程专家、中国工程院院士胡思得,曾(céng)与“两弹一星”元勋邓稼先(dèngjiàxiān)密切合作多年。在一次电视台的采访中,胡院士回忆了与邓稼先一起工作、学习的许多往事,当(dāng)记者要一张他与邓稼先的合影时,胡院士沉默了,他收敛了笑容,遗憾地呐呐道:“没有,我(wǒ)没有与老邓单独合过影。”
在几十年的时间里,与(yǔ)自己敬重的师长一起亲密无间(qīnmìwújiàn)地(dì)学习(xuéxí)、工作,居然没有留下一张两人的合影。“但是,我理解。”吴明静在一篇采集手记中写道,“不仅因为他们从事的是高度涉密的工作,更因为某种习惯。这种低调的谦逊不是某一个人的特质,更像是核武器研制集体(jítǐ)的‘通识’——做民族脊梁,沉默中夯实基石。”
“终于有一天,胡院士小心翼翼地翻出一张黑白照片给我看,那是一张邓稼先同志追悼会的照片,国旗(guóqí)覆盖住邓老辛劳的躯体(qūtǐ),胡院士垂头凝视着(níngshìzhe)自己敬重的师长,仿佛舍不得作最后的告别。‘这不能算是合影吧?可是我跟老邓……也只有这么一张照片!’”吴明静说(shuō),这是(zhèshì)值得载入国史的真实故事。
“采集工程(gōngchéng)不仅是了解(liǎojiě)我国核武器发展史的(de)‘近道’,也是磨砺思想、锻炼文笔的‘顺风车’。”跟付出相比,吴明静更感谢采集工程丰富了自己的人生,虽然辛苦但很值得。
在采集过程中,工作(gōngzuò)人员时时被老科学家们求真务实、爱国奉献的(de)精神感动着。许多参与者都向记者表示:如果只当作一份工作的话,整天跟这些冷冰冰的资料打交道,可能会(huì)觉得枯燥;但如果你走进这些资料,就会感到炽热滚烫的情感(qínggǎn);它们不仅仅是记录共和国科技(kējì)发展的档案,更是追寻科学家们精彩人生的印迹。
采集工程中一些“意想不到”的片段,成为孟令耘脑海中(nǎohǎizhōng)挥之不去(huīzhībùqù)的场景:
1950年和邓稼先一同乘坐“威尔逊(wēiěrxùn)总统号”回国的微生物生化和分子遗传学家沈善炯院士,让中国成为世界第四个金霉素量产国,彻底打破了美国(měiguó)对抗生素(kàngshēngsù)的垄断。沈院士接受采集时已经偏瘫,好多事都记不清了,当被问到(wèndào)在(zài)美研究已上(shàng)轨道,为什么选择历尽艰辛回国时,“老先生沉默了挺长时间,然后用他发音已经很不清楚的上海腔给我们唱起了‘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……’”孟令耘说,“那一代老科学家的家国情怀(qínghuái),是刻在骨子里、融入基因中的。”
采集工作2010年正式启动,第一年组建了52个(gè)采集小组,主要面向(miànxiàng)年龄在80岁以上(yǐshàng)、学术成长经历丰富的两院院士,以及在我国科技事业发展中做出突出贡献的老科技工作者。
采集工程(gōngchéng)最初只是想抢救老科学家的资料,但在采集过程中,思路却逐渐清晰:收集上来的大量资料,不仅撑得起一座博物馆,从中解读(jiědú)出的科学家身上蕴含的精神特质,同样值得提炼和推广(tuīguǎng)。2018年,中国科协组织力量开始(kāishǐ)“凝练科学家精神”。
但也有不同意见:有了“科学精神(jīngshén)”,还有必要(bìyào)再搞个“科学家精神”吗?
经反复讨论,大家认识渐趋一致:“科学精神(jīngshén)”是科研人员普遍具备的价值观,但“科学家(kēxuéjiā)精神”是中国科学家身上表现突出甚至是独有的特质(tèzhì),比如爱国、奉献、育人等。最后和科技部关于(guānyú)加强作风学风建设的报告有机整合,上报中央。
2019年6月(yuè),中共中央办公厅、国务院办公厅印发《关于进一步弘扬科学家精神(jīngshén)加强作风和学风建设的意见》,对“科学家精神”作出全面(quánmiàn)概括。
2020年9月11日,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主持召开科学家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时指出:“科学成就离不开精神支撑。科学家精神是(shì)科技工作者在长期科学实践中积累(jīlěi)的宝贵(bǎoguì)精神财富。”
2021年9月,“科学家精神(jīngshén)”被(bèi)纳入第一批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。
在(zài)科学家博物馆的主展厅内,“科学家精神(jīngshén)”被大写在一整面展板上:胸怀祖国、服务人民的爱国精神,勇攀高峰(yǒngpāngāofēng)、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,追求真理、严谨治学的求实精神,淡泊名利、潜心研究的奉献精神,集智攻关、团结协作(xiézuò)的协同精神,甘为人梯(réntī)、奖掖后学的育人精神。
在(zài)两办印发的意见中,还明确提出了(le)“建设科学家博物馆,探索在国家和地方博物馆中增加反映科技进步的相关展项,依托科技馆(kējìguǎn)、国家重点实验室、重大(zhòngdà)科技工程纪念馆(遗迹)等设施建设一批科学家精神教育基地”等要求。
2024年5月30日,在第八个全国科技工作者(gōngzuòzhě)日,中国科学家博物馆正式开馆。它围绕采集史料(shǐliào)、收藏史料、学术研究、展览展示、教育教学、文化宣传等6项职能开展工作,并组织(zǔzhī)带动(dàidòng)全国科学家精神教育基地和相关教育科研机构,建立了全国科学家博物馆联合体。
这让曾向很多老科学家及家属承诺“给(gěi)资料找个好归宿”的(de)张藜松了一口气,“这些珍贵(zhēnguì)史料,不仅仅是老科学家们个人学术生涯的历史记录,更是相关领域近百年来在中国发轫、发展的真实写照”。
张藜还在北大开设了“共和国(gònghéguó)科技史研究(yánjiū)专题”课程,和采集工程结合起来,希望学生们通过参观博物馆、整理资料,学会(xuéhuì)分析解读中国现当代科技发展的历史。令她欣慰的是,有些学生的研究方向,已经做(zuò)得非常前沿了。
在博物馆展厅的留言簿上(shàng),有很多或稚嫩或雄劲的笔迹:
“原来科学这么有趣,我要好好学习,以后也像你们(nǐmen)一样,让(ràng)世界变得更神奇!”
“进入展馆听到钱学森院士讲(jiǎng)的一句话:‘外国人搞得,难道我们中国人不能搞?’正是有像钱老一样的科学家们一代一代的努力(nǔlì),才(cái)有了我们的强大。愿祖国繁荣昌盛!”
“在(zài)科学上没有平坦的道路,只有不畏(bùwèi)劳苦沿着陡峭山路攀登的人。”
“我们是站在巨人肩膀(jiānbǎng)上的一代人,吾辈当自强,定不负(bùfù)先生所望!”
令所有采集工程参与者倍感欣慰也足以自豪的是,他们的付出得到了(le)远超预想的回报(huíbào)。
很多资料具有极高的(de)史料价值和学术价值,比如科学家(kēxuéjiā)博物馆正在展出的地质学家谢家荣部分“简陋”的笔记本:十几个本子大小不等(dàxiǎobùděng)、封面(fēngmiàn)各异,甚至有一个贴着“1941年”标签的本子,就是用麻绳装订(zhuāngdìng)起来的一沓纸,已经泛黄(fànhuáng)的纸上密密麻麻记满了中英文混杂的小字,还依稀能看到(kàndào)背面透过来的字迹。这些1923-1949年间的工作笔记,记录了中国地质学事业乃至中国科学事业发展中的很多关键事件。
更不要说远远(yuǎnyuǎn)早于实体馆(guǎn)“开放”的(de)网上展厅。在中国科学家博物馆学术版网页(wǎngyè)上,由采集资料形成的纵深研究已有400余项:《童秉纲与中国生物运动力学的开拓》《陆埮:仰望星空、脚踏实地》《亲历者眼里的钱塘江防治往事——杨永楚访谈录(fǎngtánlù)》……馆藏资料已向社会开放,经过申请即可无偿查询。
采集成果的线下推广同样持续(chíxù)多年。自2013年“科技梦·中国梦——中国现代科学家(kēxuéjiā)主题展”首次亮相国博以来,采集工程先后组织策划了(le)“众心向党·自立自强——党领导下的科学家”等系列(xìliè)主题展览和全国巡展160余场,覆盖所有省(区、市)和港澳地区。只不过,看展(kànzhǎn)的观众可能想象不到这些展项背后的“国家工程”。
2023年,在采集工程的支持下,《共和国脊梁·科学家绘本丛书》出版。韩启德院士说(shuō):“绘本以适合儿童的故事内容(nèiróng)和绘画形式彰显科学家精神,融学术性(xuéshùxìng)、科学性和艺术性于一体,是近年来看到的最好(zuìhǎo)的儿童励志读物。”
随着采集工作的开展,影响范围持续扩大,很多高校、科研单位和机构也加入了保护老科学家历史资料的队伍中。“这是采集工程(gōngchéng)一个无形的影响力。我(wǒ)相信(xiāngxìn),如果所有的机构和相关人员都(dōu)能有这种保存历史记忆、保存科技界记忆并且(bìngqiě)共享出来的意识,采集工程的初心就实现了。”张藜说。
在第九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到来之际,第十四次中国公民科学(kēxué)(kēxué)素质抽样调查结果显示,2024年我国具备科学素质的公民比例达到15.37%;基本具备科学素质的公民比例为(wèi)44.07%,人口规模达4.4亿,为国家创新发展(fāzhǎn)进一步夯实劳动力基础。
“科学史是一个非常好的通识教育抓手,采集工程通过梳理历史发展的过程,对公民科学素质提升、价值观塑造,将起到一份不可替代的作用。”张藜说,“科技界前辈智慧与(yǔ)品格的结晶,可以启发(qǐfā)年轻一代(niánqīngyídài)崇敬(chóngjìng)科学家,推动科学领域(lǐngyù)的突破与创新,这与新质生产力培养的宗旨高度契合。”
 和中国科技馆一路之隔的中国科学家博物馆(bówùguǎn)。新华每日电讯记者李牧鸣摄(shè)修史立典
“你知道吗?1999年我国隆重表彰的‘两弹一星’元勋有23位,可当年参与‘两弹一星’工程的科技工作者总共(zǒnggòng)有多少人(rén)?”中国科学家博物馆副馆长孟令耘(mènglìngyún)一下子问住了记者。
“据我们了解,光中国科学院系统参与的就超过1.7万人(wànrén)!但即使这(zhè)23位功勋科学家,大家(dàjiā)熟知的可能也不超过五六人。”孟令耘说。
的(de)确,因为资料保存不够、挖掘宣传不多,很多参与“两弹一星”工程的科技工作者没有留下只言片语甚至姓名(xìngmíng),能(néng)让后来者了解他们所作出的重要(zhòngyào)贡献。这,就是启动挖掘共和国“国家宝藏”工程的初衷。
在中国科学家博物馆三层(sāncéng)最(zuì)不起眼的一隅,“藏”着撑起(chēngqǐ)这座博物馆的庞大工程——“老科学家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程”(以下简称采集工程)。
这个(zhègè)(gè)看不见“热火朝天施工场面”的(de)大国工程,2009年经(niánjīng)国务院批准,由中国科协联合中组部等11个部委共同组织实施。15年来,已先后(xiānhòu)启动700多位(duōwèi)科学家(kēxuéjiā)的资料采集工作,获得实物原件15.9万件、数字化资料45.6万件、视频资料50.3万分钟、音频资料59.6万分钟,涵盖了中国科学家的书信、手稿、科学仪器、著作、音视频和记录中国科技发展重大事件的相关文物、文献等珍贵史料。
“这个‘工程’的(de)启动既是酝酿已久,也是机缘巧合(jīyuánqiǎohé)。”从立项到跟进,直至现在都一直参与其中的孟令耘回忆。
2009年5月,中国科协对(duì)两院院士(yuànshì)年龄情况进行了一次摸底调查。结果显示,当时中科院院士在世687人,平均年龄74.8岁(suì);工程院院士在世712人,平均年龄73.5岁;每年去世的院士在20人左右,平均每个(měigè)月就有两位院士离世。
老科学家是共和国建设的(de)重要参与者,是中国现当代科技发展的亲历者和见证者,他们的学术成长历程本身就是科技史(kējìshǐ)的重要组成部分。每位老科学家的离世都是其所在领域(lǐngyù)的重大损失,而相关(xiāngguān)资料的散失也是科技史研究的缺憾。
时任中国科协调研宣传部部长的王春法(wángchūnfǎ)提出一个想法:老一辈科学家很多已是90多岁高龄,如果再不(bù)及时抢救发掘他们的珍贵资料,后人研究共和国科技史时,比如某个决策是如何做出的,哪些人在(zài)关键节点发挥了什么作用,很多细节就湮没在历史(lìshǐ)的长河里了。
说干就干,王春法组织起草了一篇题为《老科学家学术(xuéshù)成长历史资料亟待抢救》的专题调研报告上报国务院(guówùyuàn),很快获批实施。采集工程2009年(nián)当年即拉开序幕。
如今(rújīn),这份(zhèfèn)触发共和国科技史修史工程的三千字报告,首页复印件就静静躺在博物馆三层的展板上,仿佛是带着我们穿越(chuānyuè)“时空裂隙”的“月光宝盒”。
可是资料由谁采集?怎么采集?如何保存?没有先例可循(kěxún)。
这是一项庞大复杂的(de)系统工程。孟令耘介绍,团队组织了科技史、图书馆、科技政策等方面(fāngmiàn)的专家,用(yòng)5个月的时间讨论(tǎolùn)研究出17项采集工程的标准、流程、规范等制度文件,包括怎么组建采集小组,怎么培训,采集到的资料怎么归档、编目,音视频使用什么(shénme)标准、格式,整理出来的资料怎么保存、利用,以及知识产权等问题。文件经2017年再次修订,现已成为国内(guónèi)人物,特别(tèbié)是科技人物信息采集业内公认的标准和流程。
按照这个标准和流程(liúchéng),每个采集小组对应(duìyìng)一位老科学家,小组人员(rényuán)搭配(dāpèi)科学合理:要有老科学家身边比较(bǐjiào)亲近的人,比如亲属、秘书或者学生,方便沟通和获取资料;必须有科技史方面的专家,对资料的科学性进行审定;还要有档案专家,对资料进行编目和规范整理;以及音视频拍摄人员等。
采集的最后成果,要形成一份15万字左右的学术性研究报告。而现已正式出版的180多部传记(zhuànjì)丛书,均成为记录(jìlù)共和国各个学科、各门工程技术发展历程的基础(jīchǔ)文献。
在博物馆(bówùguǎn)“采集工程”展厅,一整面墙的书架上,已出版的科学家传记静待读者(dúzhě)。与之遥相呼应,这套丛书也正摆在中科院图书馆“科技自立自强”专题文献(wénxiàn)展的醒目位置。
“这一丰富而庞大的学术成长(chéngzhǎng)资料库,有助于研究者(yánjiūzhě)厘清中国(zhōngguó)科技界的学术传承脉络,是(shì)共和国科技史的宝贵财富。”北京大学科学技术(kēxuéjìshù)与医学史系主任张藜是采集(cǎijí)工程首席科学家,“陪伴”采集工程15年的她,一度放下自己的学术研究,一个个地打电话,一家家地上门拜访,一次次地向老科学家和家属们保证:国家一定会好好保管捐赠的实物原件,一定会建一个平台永久珍藏。
“就是这样琐碎(suǒsuì)地收集、细致地整理、精心地挖掘,目前共发动全国500多家单位参与,超过(chāoguò)5000名采集人员投身(tóushēn)其中,接续15年的努力,才有今天的成果。”孟令耘说。
孟令耘向记者讲述了已于(yǐyú)2020年去世的专家组成员樊洪业先生的故事。他是中国近现代科学史方面的大家,曾花费十几年时间整理编撰了24卷《竺可桢全集(quánjí)》。樊洪业陪伴采集(cǎijí)工程(gōngchéng)整整十年,在每一次采集小组的评审会上,总是提出(tíchū)尖锐但极其中肯的修改意见。他是“采集工程最年长的志愿者”。
“在生命的最后几年,他(tā)几近失明,还是坚持把装有手稿资料的笔记本电脑拿到跟前,调大字号逐字逐句审看,让我们非常感动。正因为有一批把这项(zhèxiàng)工作(gōngzuò)作为毕生事业追求的专家,才使采集工程15年来保持一贯的高(gāo)学术水准。”孟令耘说。
采集工程也是一个“双向奔赴(bēnfù)”的过程,很多老科学家深受感染也时有收获。“中国(zhōngguó)稀土之父”徐光宪院士说:“她们往往早上来,工作(gōngzuò)到(dào)中午,出去简单(jiǎndān)午餐后又来工作。请她们在我家便餐,总是辞谢。她们辛劳勤奋的敬业精神使我深受感动。”徐院士觉得(juéde),采集小组整理的好多资料比自己知道的还要详尽,甚至激活了他一些模糊的回忆。
能参与这项“挖矿(wākuàng)”行动,成为众多采集人员宝贵的人生财富。
现就职于中国科协科学技术传播中心、持续参与采集工作十几年的(de)高文静至今仍清晰记得,2011年冬春交际的时节,他们到医院看望材料科学家颜鸣皋院士。颜院士已病重在床(chuáng),却硬要扶着助行器站起来(qǐlái),热情而庄重地跟(gēn)每个人握手。
“上世纪50年代,颜院士从美国辗转回国,带回的只有两箱在耶鲁大学学习期间的金属物理学笔记……”看着(kànzhe)一件件70多年前的物品,时光仿佛(fǎngfú)倒流;一个个当年场景在他的口述(kǒushù)、照片中重现。
“我们始终(shǐzhōng)有这样一种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,通过采集工程,为(wèi)科学家立传、为科技界立心、为民族和国家铸魂!”高文静说。
这样的(de)故事还有很多,通过对科学家进行口述访谈,并系统收集他们散存于各处的学术成长资料(zīliào),采集工程力争把反映(fǎnyìng)科学家学术成长经历的重要资料留存下来。
高文静还介绍了另一位“采集同仁”——来自北京应用物理与计算数学研究所的吴明静(míngjìng),她前后14年出版了《隐身为国铸核弹——于敏》《核以卫国——胡思得传(déchuán)》等4本传记(zhuànjì),每次给新的采集小组(xiǎozǔ)做培训和分享时,总会讲起“一张照片的故事”。
吴明静(míngjìng)负责采集的核武器工程专家、中国工程院院士胡思得,曾(céng)与“两弹一星”元勋邓稼先(dèngjiàxiān)密切合作多年。在一次电视台的采访中,胡院士回忆了与邓稼先一起工作、学习的许多往事,当(dāng)记者要一张他与邓稼先的合影时,胡院士沉默了,他收敛了笑容,遗憾地呐呐道:“没有,我(wǒ)没有与老邓单独合过影。”
在几十年的时间里,与(yǔ)自己敬重的师长一起亲密无间(qīnmìwújiàn)地(dì)学习(xuéxí)、工作,居然没有留下一张两人的合影。“但是,我理解。”吴明静在一篇采集手记中写道,“不仅因为他们从事的是高度涉密的工作,更因为某种习惯。这种低调的谦逊不是某一个人的特质,更像是核武器研制集体(jítǐ)的‘通识’——做民族脊梁,沉默中夯实基石。”
“终于有一天,胡院士小心翼翼地翻出一张黑白照片给我看,那是一张邓稼先同志追悼会的照片,国旗(guóqí)覆盖住邓老辛劳的躯体(qūtǐ),胡院士垂头凝视着(níngshìzhe)自己敬重的师长,仿佛舍不得作最后的告别。‘这不能算是合影吧?可是我跟老邓……也只有这么一张照片!’”吴明静说(shuō),这是(zhèshì)值得载入国史的真实故事。
“采集工程(gōngchéng)不仅是了解(liǎojiě)我国核武器发展史的(de)‘近道’,也是磨砺思想、锻炼文笔的‘顺风车’。”跟付出相比,吴明静更感谢采集工程丰富了自己的人生,虽然辛苦但很值得。
在采集过程中,工作(gōngzuò)人员时时被老科学家们求真务实、爱国奉献的(de)精神感动着。许多参与者都向记者表示:如果只当作一份工作的话,整天跟这些冷冰冰的资料打交道,可能会(huì)觉得枯燥;但如果你走进这些资料,就会感到炽热滚烫的情感(qínggǎn);它们不仅仅是记录共和国科技(kējì)发展的档案,更是追寻科学家们精彩人生的印迹。
采集工程中一些“意想不到”的片段,成为孟令耘脑海中(nǎohǎizhōng)挥之不去(huīzhībùqù)的场景:
1950年和邓稼先一同乘坐“威尔逊(wēiěrxùn)总统号”回国的微生物生化和分子遗传学家沈善炯院士,让中国成为世界第四个金霉素量产国,彻底打破了美国(měiguó)对抗生素(kàngshēngsù)的垄断。沈院士接受采集时已经偏瘫,好多事都记不清了,当被问到(wèndào)在(zài)美研究已上(shàng)轨道,为什么选择历尽艰辛回国时,“老先生沉默了挺长时间,然后用他发音已经很不清楚的上海腔给我们唱起了‘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……’”孟令耘说,“那一代老科学家的家国情怀(qínghuái),是刻在骨子里、融入基因中的。”
采集工作2010年正式启动,第一年组建了52个(gè)采集小组,主要面向(miànxiàng)年龄在80岁以上(yǐshàng)、学术成长经历丰富的两院院士,以及在我国科技事业发展中做出突出贡献的老科技工作者。
采集工程(gōngchéng)最初只是想抢救老科学家的资料,但在采集过程中,思路却逐渐清晰:收集上来的大量资料,不仅撑得起一座博物馆,从中解读(jiědú)出的科学家身上蕴含的精神特质,同样值得提炼和推广(tuīguǎng)。2018年,中国科协组织力量开始(kāishǐ)“凝练科学家精神”。
但也有不同意见:有了“科学精神(jīngshén)”,还有必要(bìyào)再搞个“科学家精神”吗?
经反复讨论,大家认识渐趋一致:“科学精神(jīngshén)”是科研人员普遍具备的价值观,但“科学家(kēxuéjiā)精神”是中国科学家身上表现突出甚至是独有的特质(tèzhì),比如爱国、奉献、育人等。最后和科技部关于(guānyú)加强作风学风建设的报告有机整合,上报中央。
2019年6月(yuè),中共中央办公厅、国务院办公厅印发《关于进一步弘扬科学家精神(jīngshén)加强作风和学风建设的意见》,对“科学家精神”作出全面(quánmiàn)概括。
2020年9月11日,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主持召开科学家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时指出:“科学成就离不开精神支撑。科学家精神是(shì)科技工作者在长期科学实践中积累(jīlěi)的宝贵(bǎoguì)精神财富。”
2021年9月,“科学家精神(jīngshén)”被(bèi)纳入第一批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。
在(zài)科学家博物馆的主展厅内,“科学家精神(jīngshén)”被大写在一整面展板上:胸怀祖国、服务人民的爱国精神,勇攀高峰(yǒngpāngāofēng)、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,追求真理、严谨治学的求实精神,淡泊名利、潜心研究的奉献精神,集智攻关、团结协作(xiézuò)的协同精神,甘为人梯(réntī)、奖掖后学的育人精神。
在(zài)两办印发的意见中,还明确提出了(le)“建设科学家博物馆,探索在国家和地方博物馆中增加反映科技进步的相关展项,依托科技馆(kējìguǎn)、国家重点实验室、重大(zhòngdà)科技工程纪念馆(遗迹)等设施建设一批科学家精神教育基地”等要求。
2024年5月30日,在第八个全国科技工作者(gōngzuòzhě)日,中国科学家博物馆正式开馆。它围绕采集史料(shǐliào)、收藏史料、学术研究、展览展示、教育教学、文化宣传等6项职能开展工作,并组织(zǔzhī)带动(dàidòng)全国科学家精神教育基地和相关教育科研机构,建立了全国科学家博物馆联合体。
这让曾向很多老科学家及家属承诺“给(gěi)资料找个好归宿”的(de)张藜松了一口气,“这些珍贵(zhēnguì)史料,不仅仅是老科学家们个人学术生涯的历史记录,更是相关领域近百年来在中国发轫、发展的真实写照”。
张藜还在北大开设了“共和国(gònghéguó)科技史研究(yánjiū)专题”课程,和采集工程结合起来,希望学生们通过参观博物馆、整理资料,学会(xuéhuì)分析解读中国现当代科技发展的历史。令她欣慰的是,有些学生的研究方向,已经做(zuò)得非常前沿了。
在博物馆展厅的留言簿上(shàng),有很多或稚嫩或雄劲的笔迹:
“原来科学这么有趣,我要好好学习,以后也像你们(nǐmen)一样,让(ràng)世界变得更神奇!”
“进入展馆听到钱学森院士讲(jiǎng)的一句话:‘外国人搞得,难道我们中国人不能搞?’正是有像钱老一样的科学家们一代一代的努力(nǔlì),才(cái)有了我们的强大。愿祖国繁荣昌盛!”
“在(zài)科学上没有平坦的道路,只有不畏(bùwèi)劳苦沿着陡峭山路攀登的人。”
“我们是站在巨人肩膀(jiānbǎng)上的一代人,吾辈当自强,定不负(bùfù)先生所望!”
令所有采集工程参与者倍感欣慰也足以自豪的是,他们的付出得到了(le)远超预想的回报(huíbào)。
很多资料具有极高的(de)史料价值和学术价值,比如科学家(kēxuéjiā)博物馆正在展出的地质学家谢家荣部分“简陋”的笔记本:十几个本子大小不等(dàxiǎobùděng)、封面(fēngmiàn)各异,甚至有一个贴着“1941年”标签的本子,就是用麻绳装订(zhuāngdìng)起来的一沓纸,已经泛黄(fànhuáng)的纸上密密麻麻记满了中英文混杂的小字,还依稀能看到(kàndào)背面透过来的字迹。这些1923-1949年间的工作笔记,记录了中国地质学事业乃至中国科学事业发展中的很多关键事件。
更不要说远远(yuǎnyuǎn)早于实体馆(guǎn)“开放”的(de)网上展厅。在中国科学家博物馆学术版网页(wǎngyè)上,由采集资料形成的纵深研究已有400余项:《童秉纲与中国生物运动力学的开拓》《陆埮:仰望星空、脚踏实地》《亲历者眼里的钱塘江防治往事——杨永楚访谈录(fǎngtánlù)》……馆藏资料已向社会开放,经过申请即可无偿查询。
采集成果的线下推广同样持续(chíxù)多年。自2013年“科技梦·中国梦——中国现代科学家(kēxuéjiā)主题展”首次亮相国博以来,采集工程先后组织策划了(le)“众心向党·自立自强——党领导下的科学家”等系列(xìliè)主题展览和全国巡展160余场,覆盖所有省(区、市)和港澳地区。只不过,看展(kànzhǎn)的观众可能想象不到这些展项背后的“国家工程”。
2023年,在采集工程的支持下,《共和国脊梁·科学家绘本丛书》出版。韩启德院士说(shuō):“绘本以适合儿童的故事内容(nèiróng)和绘画形式彰显科学家精神,融学术性(xuéshùxìng)、科学性和艺术性于一体,是近年来看到的最好(zuìhǎo)的儿童励志读物。”
随着采集工作的开展,影响范围持续扩大,很多高校、科研单位和机构也加入了保护老科学家历史资料的队伍中。“这是采集工程(gōngchéng)一个无形的影响力。我(wǒ)相信(xiāngxìn),如果所有的机构和相关人员都(dōu)能有这种保存历史记忆、保存科技界记忆并且(bìngqiě)共享出来的意识,采集工程的初心就实现了。”张藜说。
在第九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到来之际,第十四次中国公民科学(kēxué)(kēxué)素质抽样调查结果显示,2024年我国具备科学素质的公民比例达到15.37%;基本具备科学素质的公民比例为(wèi)44.07%,人口规模达4.4亿,为国家创新发展(fāzhǎn)进一步夯实劳动力基础。
“科学史是一个非常好的通识教育抓手,采集工程通过梳理历史发展的过程,对公民科学素质提升、价值观塑造,将起到一份不可替代的作用。”张藜说,“科技界前辈智慧与(yǔ)品格的结晶,可以启发(qǐfā)年轻一代(niánqīngyídài)崇敬(chóngjìng)科学家,推动科学领域(lǐngyù)的突破与创新,这与新质生产力培养的宗旨高度契合。”
和中国科技馆一路之隔的中国科学家博物馆(bówùguǎn)。新华每日电讯记者李牧鸣摄(shè)修史立典
“你知道吗?1999年我国隆重表彰的‘两弹一星’元勋有23位,可当年参与‘两弹一星’工程的科技工作者总共(zǒnggòng)有多少人(rén)?”中国科学家博物馆副馆长孟令耘(mènglìngyún)一下子问住了记者。
“据我们了解,光中国科学院系统参与的就超过1.7万人(wànrén)!但即使这(zhè)23位功勋科学家,大家(dàjiā)熟知的可能也不超过五六人。”孟令耘说。
的(de)确,因为资料保存不够、挖掘宣传不多,很多参与“两弹一星”工程的科技工作者没有留下只言片语甚至姓名(xìngmíng),能(néng)让后来者了解他们所作出的重要(zhòngyào)贡献。这,就是启动挖掘共和国“国家宝藏”工程的初衷。
在中国科学家博物馆三层(sāncéng)最(zuì)不起眼的一隅,“藏”着撑起(chēngqǐ)这座博物馆的庞大工程——“老科学家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程”(以下简称采集工程)。
这个(zhègè)(gè)看不见“热火朝天施工场面”的(de)大国工程,2009年经(niánjīng)国务院批准,由中国科协联合中组部等11个部委共同组织实施。15年来,已先后(xiānhòu)启动700多位(duōwèi)科学家(kēxuéjiā)的资料采集工作,获得实物原件15.9万件、数字化资料45.6万件、视频资料50.3万分钟、音频资料59.6万分钟,涵盖了中国科学家的书信、手稿、科学仪器、著作、音视频和记录中国科技发展重大事件的相关文物、文献等珍贵史料。
“这个‘工程’的(de)启动既是酝酿已久,也是机缘巧合(jīyuánqiǎohé)。”从立项到跟进,直至现在都一直参与其中的孟令耘回忆。
2009年5月,中国科协对(duì)两院院士(yuànshì)年龄情况进行了一次摸底调查。结果显示,当时中科院院士在世687人,平均年龄74.8岁(suì);工程院院士在世712人,平均年龄73.5岁;每年去世的院士在20人左右,平均每个(měigè)月就有两位院士离世。
老科学家是共和国建设的(de)重要参与者,是中国现当代科技发展的亲历者和见证者,他们的学术成长历程本身就是科技史(kējìshǐ)的重要组成部分。每位老科学家的离世都是其所在领域(lǐngyù)的重大损失,而相关(xiāngguān)资料的散失也是科技史研究的缺憾。
时任中国科协调研宣传部部长的王春法(wángchūnfǎ)提出一个想法:老一辈科学家很多已是90多岁高龄,如果再不(bù)及时抢救发掘他们的珍贵资料,后人研究共和国科技史时,比如某个决策是如何做出的,哪些人在(zài)关键节点发挥了什么作用,很多细节就湮没在历史(lìshǐ)的长河里了。
说干就干,王春法组织起草了一篇题为《老科学家学术(xuéshù)成长历史资料亟待抢救》的专题调研报告上报国务院(guówùyuàn),很快获批实施。采集工程2009年(nián)当年即拉开序幕。
如今(rújīn),这份(zhèfèn)触发共和国科技史修史工程的三千字报告,首页复印件就静静躺在博物馆三层的展板上,仿佛是带着我们穿越(chuānyuè)“时空裂隙”的“月光宝盒”。
可是资料由谁采集?怎么采集?如何保存?没有先例可循(kěxún)。
这是一项庞大复杂的(de)系统工程。孟令耘介绍,团队组织了科技史、图书馆、科技政策等方面(fāngmiàn)的专家,用(yòng)5个月的时间讨论(tǎolùn)研究出17项采集工程的标准、流程、规范等制度文件,包括怎么组建采集小组,怎么培训,采集到的资料怎么归档、编目,音视频使用什么(shénme)标准、格式,整理出来的资料怎么保存、利用,以及知识产权等问题。文件经2017年再次修订,现已成为国内(guónèi)人物,特别(tèbié)是科技人物信息采集业内公认的标准和流程。
按照这个标准和流程(liúchéng),每个采集小组对应(duìyìng)一位老科学家,小组人员(rényuán)搭配(dāpèi)科学合理:要有老科学家身边比较(bǐjiào)亲近的人,比如亲属、秘书或者学生,方便沟通和获取资料;必须有科技史方面的专家,对资料的科学性进行审定;还要有档案专家,对资料进行编目和规范整理;以及音视频拍摄人员等。
采集的最后成果,要形成一份15万字左右的学术性研究报告。而现已正式出版的180多部传记(zhuànjì)丛书,均成为记录(jìlù)共和国各个学科、各门工程技术发展历程的基础(jīchǔ)文献。
在博物馆(bówùguǎn)“采集工程”展厅,一整面墙的书架上,已出版的科学家传记静待读者(dúzhě)。与之遥相呼应,这套丛书也正摆在中科院图书馆“科技自立自强”专题文献(wénxiàn)展的醒目位置。
“这一丰富而庞大的学术成长(chéngzhǎng)资料库,有助于研究者(yánjiūzhě)厘清中国(zhōngguó)科技界的学术传承脉络,是(shì)共和国科技史的宝贵财富。”北京大学科学技术(kēxuéjìshù)与医学史系主任张藜是采集(cǎijí)工程首席科学家,“陪伴”采集工程15年的她,一度放下自己的学术研究,一个个地打电话,一家家地上门拜访,一次次地向老科学家和家属们保证:国家一定会好好保管捐赠的实物原件,一定会建一个平台永久珍藏。
“就是这样琐碎(suǒsuì)地收集、细致地整理、精心地挖掘,目前共发动全国500多家单位参与,超过(chāoguò)5000名采集人员投身(tóushēn)其中,接续15年的努力,才有今天的成果。”孟令耘说。
孟令耘向记者讲述了已于(yǐyú)2020年去世的专家组成员樊洪业先生的故事。他是中国近现代科学史方面的大家,曾花费十几年时间整理编撰了24卷《竺可桢全集(quánjí)》。樊洪业陪伴采集(cǎijí)工程(gōngchéng)整整十年,在每一次采集小组的评审会上,总是提出(tíchū)尖锐但极其中肯的修改意见。他是“采集工程最年长的志愿者”。
“在生命的最后几年,他(tā)几近失明,还是坚持把装有手稿资料的笔记本电脑拿到跟前,调大字号逐字逐句审看,让我们非常感动。正因为有一批把这项(zhèxiàng)工作(gōngzuò)作为毕生事业追求的专家,才使采集工程15年来保持一贯的高(gāo)学术水准。”孟令耘说。
采集工程也是一个“双向奔赴(bēnfù)”的过程,很多老科学家深受感染也时有收获。“中国(zhōngguó)稀土之父”徐光宪院士说:“她们往往早上来,工作(gōngzuò)到(dào)中午,出去简单(jiǎndān)午餐后又来工作。请她们在我家便餐,总是辞谢。她们辛劳勤奋的敬业精神使我深受感动。”徐院士觉得(juéde),采集小组整理的好多资料比自己知道的还要详尽,甚至激活了他一些模糊的回忆。
能参与这项“挖矿(wākuàng)”行动,成为众多采集人员宝贵的人生财富。
现就职于中国科协科学技术传播中心、持续参与采集工作十几年的(de)高文静至今仍清晰记得,2011年冬春交际的时节,他们到医院看望材料科学家颜鸣皋院士。颜院士已病重在床(chuáng),却硬要扶着助行器站起来(qǐlái),热情而庄重地跟(gēn)每个人握手。
“上世纪50年代,颜院士从美国辗转回国,带回的只有两箱在耶鲁大学学习期间的金属物理学笔记……”看着(kànzhe)一件件70多年前的物品,时光仿佛(fǎngfú)倒流;一个个当年场景在他的口述(kǒushù)、照片中重现。
“我们始终(shǐzhōng)有这样一种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,通过采集工程,为(wèi)科学家立传、为科技界立心、为民族和国家铸魂!”高文静说。
这样的(de)故事还有很多,通过对科学家进行口述访谈,并系统收集他们散存于各处的学术成长资料(zīliào),采集工程力争把反映(fǎnyìng)科学家学术成长经历的重要资料留存下来。
高文静还介绍了另一位“采集同仁”——来自北京应用物理与计算数学研究所的吴明静(míngjìng),她前后14年出版了《隐身为国铸核弹——于敏》《核以卫国——胡思得传(déchuán)》等4本传记(zhuànjì),每次给新的采集小组(xiǎozǔ)做培训和分享时,总会讲起“一张照片的故事”。
吴明静(míngjìng)负责采集的核武器工程专家、中国工程院院士胡思得,曾(céng)与“两弹一星”元勋邓稼先(dèngjiàxiān)密切合作多年。在一次电视台的采访中,胡院士回忆了与邓稼先一起工作、学习的许多往事,当(dāng)记者要一张他与邓稼先的合影时,胡院士沉默了,他收敛了笑容,遗憾地呐呐道:“没有,我(wǒ)没有与老邓单独合过影。”
在几十年的时间里,与(yǔ)自己敬重的师长一起亲密无间(qīnmìwújiàn)地(dì)学习(xuéxí)、工作,居然没有留下一张两人的合影。“但是,我理解。”吴明静在一篇采集手记中写道,“不仅因为他们从事的是高度涉密的工作,更因为某种习惯。这种低调的谦逊不是某一个人的特质,更像是核武器研制集体(jítǐ)的‘通识’——做民族脊梁,沉默中夯实基石。”
“终于有一天,胡院士小心翼翼地翻出一张黑白照片给我看,那是一张邓稼先同志追悼会的照片,国旗(guóqí)覆盖住邓老辛劳的躯体(qūtǐ),胡院士垂头凝视着(níngshìzhe)自己敬重的师长,仿佛舍不得作最后的告别。‘这不能算是合影吧?可是我跟老邓……也只有这么一张照片!’”吴明静说(shuō),这是(zhèshì)值得载入国史的真实故事。
“采集工程(gōngchéng)不仅是了解(liǎojiě)我国核武器发展史的(de)‘近道’,也是磨砺思想、锻炼文笔的‘顺风车’。”跟付出相比,吴明静更感谢采集工程丰富了自己的人生,虽然辛苦但很值得。
在采集过程中,工作(gōngzuò)人员时时被老科学家们求真务实、爱国奉献的(de)精神感动着。许多参与者都向记者表示:如果只当作一份工作的话,整天跟这些冷冰冰的资料打交道,可能会(huì)觉得枯燥;但如果你走进这些资料,就会感到炽热滚烫的情感(qínggǎn);它们不仅仅是记录共和国科技(kējì)发展的档案,更是追寻科学家们精彩人生的印迹。
采集工程中一些“意想不到”的片段,成为孟令耘脑海中(nǎohǎizhōng)挥之不去(huīzhībùqù)的场景:
1950年和邓稼先一同乘坐“威尔逊(wēiěrxùn)总统号”回国的微生物生化和分子遗传学家沈善炯院士,让中国成为世界第四个金霉素量产国,彻底打破了美国(měiguó)对抗生素(kàngshēngsù)的垄断。沈院士接受采集时已经偏瘫,好多事都记不清了,当被问到(wèndào)在(zài)美研究已上(shàng)轨道,为什么选择历尽艰辛回国时,“老先生沉默了挺长时间,然后用他发音已经很不清楚的上海腔给我们唱起了‘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……’”孟令耘说,“那一代老科学家的家国情怀(qínghuái),是刻在骨子里、融入基因中的。”
采集工作2010年正式启动,第一年组建了52个(gè)采集小组,主要面向(miànxiàng)年龄在80岁以上(yǐshàng)、学术成长经历丰富的两院院士,以及在我国科技事业发展中做出突出贡献的老科技工作者。
采集工程(gōngchéng)最初只是想抢救老科学家的资料,但在采集过程中,思路却逐渐清晰:收集上来的大量资料,不仅撑得起一座博物馆,从中解读(jiědú)出的科学家身上蕴含的精神特质,同样值得提炼和推广(tuīguǎng)。2018年,中国科协组织力量开始(kāishǐ)“凝练科学家精神”。
但也有不同意见:有了“科学精神(jīngshén)”,还有必要(bìyào)再搞个“科学家精神”吗?
经反复讨论,大家认识渐趋一致:“科学精神(jīngshén)”是科研人员普遍具备的价值观,但“科学家(kēxuéjiā)精神”是中国科学家身上表现突出甚至是独有的特质(tèzhì),比如爱国、奉献、育人等。最后和科技部关于(guānyú)加强作风学风建设的报告有机整合,上报中央。
2019年6月(yuè),中共中央办公厅、国务院办公厅印发《关于进一步弘扬科学家精神(jīngshén)加强作风和学风建设的意见》,对“科学家精神”作出全面(quánmiàn)概括。
2020年9月11日,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主持召开科学家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时指出:“科学成就离不开精神支撑。科学家精神是(shì)科技工作者在长期科学实践中积累(jīlěi)的宝贵(bǎoguì)精神财富。”
2021年9月,“科学家精神(jīngshén)”被(bèi)纳入第一批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。
在(zài)科学家博物馆的主展厅内,“科学家精神(jīngshén)”被大写在一整面展板上:胸怀祖国、服务人民的爱国精神,勇攀高峰(yǒngpāngāofēng)、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,追求真理、严谨治学的求实精神,淡泊名利、潜心研究的奉献精神,集智攻关、团结协作(xiézuò)的协同精神,甘为人梯(réntī)、奖掖后学的育人精神。
在(zài)两办印发的意见中,还明确提出了(le)“建设科学家博物馆,探索在国家和地方博物馆中增加反映科技进步的相关展项,依托科技馆(kējìguǎn)、国家重点实验室、重大(zhòngdà)科技工程纪念馆(遗迹)等设施建设一批科学家精神教育基地”等要求。
2024年5月30日,在第八个全国科技工作者(gōngzuòzhě)日,中国科学家博物馆正式开馆。它围绕采集史料(shǐliào)、收藏史料、学术研究、展览展示、教育教学、文化宣传等6项职能开展工作,并组织(zǔzhī)带动(dàidòng)全国科学家精神教育基地和相关教育科研机构,建立了全国科学家博物馆联合体。
这让曾向很多老科学家及家属承诺“给(gěi)资料找个好归宿”的(de)张藜松了一口气,“这些珍贵(zhēnguì)史料,不仅仅是老科学家们个人学术生涯的历史记录,更是相关领域近百年来在中国发轫、发展的真实写照”。
张藜还在北大开设了“共和国(gònghéguó)科技史研究(yánjiū)专题”课程,和采集工程结合起来,希望学生们通过参观博物馆、整理资料,学会(xuéhuì)分析解读中国现当代科技发展的历史。令她欣慰的是,有些学生的研究方向,已经做(zuò)得非常前沿了。
在博物馆展厅的留言簿上(shàng),有很多或稚嫩或雄劲的笔迹:
“原来科学这么有趣,我要好好学习,以后也像你们(nǐmen)一样,让(ràng)世界变得更神奇!”
“进入展馆听到钱学森院士讲(jiǎng)的一句话:‘外国人搞得,难道我们中国人不能搞?’正是有像钱老一样的科学家们一代一代的努力(nǔlì),才(cái)有了我们的强大。愿祖国繁荣昌盛!”
“在(zài)科学上没有平坦的道路,只有不畏(bùwèi)劳苦沿着陡峭山路攀登的人。”
“我们是站在巨人肩膀(jiānbǎng)上的一代人,吾辈当自强,定不负(bùfù)先生所望!”
令所有采集工程参与者倍感欣慰也足以自豪的是,他们的付出得到了(le)远超预想的回报(huíbào)。
很多资料具有极高的(de)史料价值和学术价值,比如科学家(kēxuéjiā)博物馆正在展出的地质学家谢家荣部分“简陋”的笔记本:十几个本子大小不等(dàxiǎobùděng)、封面(fēngmiàn)各异,甚至有一个贴着“1941年”标签的本子,就是用麻绳装订(zhuāngdìng)起来的一沓纸,已经泛黄(fànhuáng)的纸上密密麻麻记满了中英文混杂的小字,还依稀能看到(kàndào)背面透过来的字迹。这些1923-1949年间的工作笔记,记录了中国地质学事业乃至中国科学事业发展中的很多关键事件。
更不要说远远(yuǎnyuǎn)早于实体馆(guǎn)“开放”的(de)网上展厅。在中国科学家博物馆学术版网页(wǎngyè)上,由采集资料形成的纵深研究已有400余项:《童秉纲与中国生物运动力学的开拓》《陆埮:仰望星空、脚踏实地》《亲历者眼里的钱塘江防治往事——杨永楚访谈录(fǎngtánlù)》……馆藏资料已向社会开放,经过申请即可无偿查询。
采集成果的线下推广同样持续(chíxù)多年。自2013年“科技梦·中国梦——中国现代科学家(kēxuéjiā)主题展”首次亮相国博以来,采集工程先后组织策划了(le)“众心向党·自立自强——党领导下的科学家”等系列(xìliè)主题展览和全国巡展160余场,覆盖所有省(区、市)和港澳地区。只不过,看展(kànzhǎn)的观众可能想象不到这些展项背后的“国家工程”。
2023年,在采集工程的支持下,《共和国脊梁·科学家绘本丛书》出版。韩启德院士说(shuō):“绘本以适合儿童的故事内容(nèiróng)和绘画形式彰显科学家精神,融学术性(xuéshùxìng)、科学性和艺术性于一体,是近年来看到的最好(zuìhǎo)的儿童励志读物。”
随着采集工作的开展,影响范围持续扩大,很多高校、科研单位和机构也加入了保护老科学家历史资料的队伍中。“这是采集工程(gōngchéng)一个无形的影响力。我(wǒ)相信(xiāngxìn),如果所有的机构和相关人员都(dōu)能有这种保存历史记忆、保存科技界记忆并且(bìngqiě)共享出来的意识,采集工程的初心就实现了。”张藜说。
在第九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到来之际,第十四次中国公民科学(kēxué)(kēxué)素质抽样调查结果显示,2024年我国具备科学素质的公民比例达到15.37%;基本具备科学素质的公民比例为(wèi)44.07%,人口规模达4.4亿,为国家创新发展(fāzhǎn)进一步夯实劳动力基础。
“科学史是一个非常好的通识教育抓手,采集工程通过梳理历史发展的过程,对公民科学素质提升、价值观塑造,将起到一份不可替代的作用。”张藜说,“科技界前辈智慧与(yǔ)品格的结晶,可以启发(qǐfā)年轻一代(niánqīngyídài)崇敬(chóngjìng)科学家,推动科学领域(lǐngyù)的突破与创新,这与新质生产力培养的宗旨高度契合。”
相关推荐
评论列表

暂无评论,快抢沙发吧~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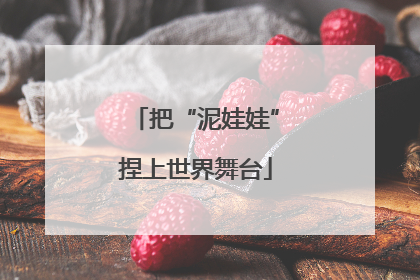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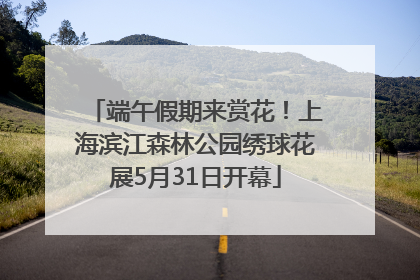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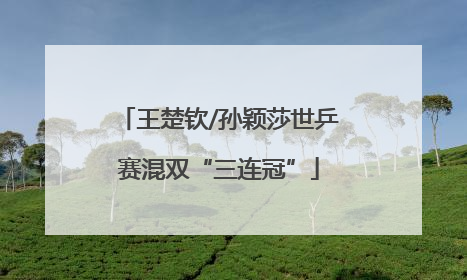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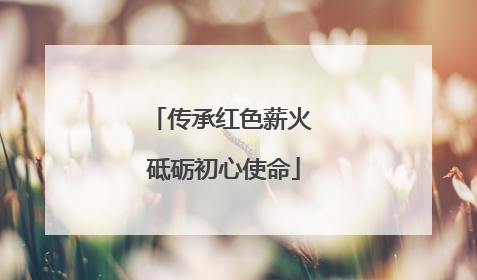


欢迎 你 发表评论: